华声在线2024年10月15日发布:聚焦行政法领域新制度——行政裁量基准,带你厘清理论理论争议
⭐发布日期:2024年10月15日 | 来源:华声在线
【新奥天天免费资料单双}】 |
【新澳门精准四肖期期中特公开】 |
【新奥门天天开奖资料大全】 | 【682222澳门彩】 | 【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最新】 | 【新澳精准资料免费提供】 | 【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最新54期】 | 【2024年澳门特马今晚开码】 | 【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最新54期129期】 | 【澳门中特网4924cc长期官网】 |
| 【新澳天天彩精准资料】 | 【2024澳门特马今晚现场回放】 | 【新澳资彩长期免费资料】 | 【爷爷生前为孙子封了坛状元酒】 | 【澳门六开彩天天开奖结果生肖卡】 | 【新澳门今晚开奖结果+开奖】 | 【澳门最精准免费资料大全旅游团】 | 【湖南发生车辆碰撞事故】 |
第二章 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
面对行政裁量基准这样一种在我国本土实践中自发生成并发展起来的新兴制度,首先必须从制度层面对其性质和功能作出合理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其存在的正当性及制度边界等问题。考察各地所推行的裁量基准实践,行政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兼具“行政自制”和“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应当定位为一种裁量性的行政自制规范,或者说是一种自制型的裁量性行政规范。由此必须站在规则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双重立场上去论证和解决裁量基准这一新兴制度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在规则主义层面,裁量基准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之治”,究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其在宪政框架下的正当性基础源于“法律保留原则”的发展与“禁止授权原则”的超越,也与我国宪政体系并不相违背。在功能主义立场,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通过“自我控权”能否解决对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即控权的有效性问题,则通过行政自制理论的合理性证明,加之内含于裁量基准中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的优越地位,亦能获得全方位澄清。然而,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自制”,亦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还必须诉诸一种正当化的制度安排,通过对裁量基准制度边界的划定及其效力的合理界定来保障其正当性的实现,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内在的制度价值和功能。通过将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规范的观察,有必要倡导一种功能主义的行政自制观,以此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的新发展。
一、行政裁量基准的性质定位
究竟什么是裁量基准,为什么需要裁量基准?这在当前的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对裁量基准性质的合理界定,直接涉及其存在的正当性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因此首先必须加以理清。
(一)理论上之分歧及辨析
对于裁量基准的性质问题,理论上有着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目前主要存在“规则化裁量基准观”和“具体化裁量基准观”这两种观点。
按照“规则化裁量基准观”,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司法所直接适用的一种立法性规则。如有学者认为:“在法律属性上,这些裁量基准有的属于规章,但更多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解释性规则。无论裁量基准以什么形式出现,从其实践效力来看,基准一旦制定颁布,便成为执法人员执法的重要依据,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这种内部适用效力,又将进一步延伸至行政相对方,因而具有了外部效力。因此可以说,裁量基准的制定,本质上就是行政立法权的行使,是行政机关对立法意图、立法目标的进一步解释和阐明。”因此,“裁量基准的制定本质上就是次级立法”。“虽然在理论上,法院对以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表现出来的裁量基准,只是可以‘参照’或‘参考’,但在实践中,法院对此类行政规则事实上没有审查权,往往给予尊重并加以适用。”(注: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基准在构筑裁量具体过程与效果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处分的一种定式。由内而外的样式,不断重复、中规中矩,也就变成了法的规范。”“承载裁量基准的形式也因此必然是多样的,可以是规章,也可以是规范性文件。”(注: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具体化裁量基准观”则认为,裁量基准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其所执行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具体而言,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执法者在行政法律规范没有提供要件—效果规定,或者虽然提供了要件—效果规定但据此不足以获得处理具体行政案件所需之完整的判断标准时,按照立法者意图、在行政法律规范所预定的范围内、以要件—效果规定的形式设定的判断标准”。其存在形式包括两种——上级行政机关事先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基准和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以行政行为理由形式设定的裁量基准。这个由上级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标准也只是一种行政内部规定,并不是具有拘束力的规则。而且,“设定裁量标准的条件、依据、范围都与行政机关所执行的特定行政法律规范有关,而非行政机关自治的结果”,裁量标准的功能,其实就是“说明理由制度的功能”(注: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王天华:《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周文明诉文山交警不按‘红头文件’行政处罚案”评析》,
http://chenyuefeng.fyfz.cn/blog/chenyuefeng/index.aspx?blogid=429327,2010年1月17日访问。 )。笔者认为,“裁量基准”一词实际上可以在两个意义上被使用。一层含义是行政机关在具体的个案裁量中所设定的作为其依据或理由的判断选择标准。它相当于上述“具体化裁量基准观”中所谓的“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以行政行为理由形式设定的裁量基准”。这实际上是任何个案裁量中都必须具备的作为其实体上的利益衡量所必备的环节,也是由裁量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所谓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主作出独立选择判断的权力。但是这种判断选择并非任意的,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标准和理由,否则就会导致裁量权的滥用或不当。而且“当裁量决定对相对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后果时,决定的作出者负有说明决定之理由的职责”(注:Geneviève Cartier,"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the Spirit of Legality: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9,24 No.3,p 325 )。譬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某种违法行为可以处以500—2000元的罚款,那么在个案裁量中究竟是处以500元、还是1000元、1500元或者是2000元的罚款,可以由行政机关判断选择,但得有个标准,比如根据情节的轻重来选择罚款的多少。这个标准构成了裁量权正当行使的理由。它一般应当由立法者通过详细的规则事先予以规定,在立法者没有提供这种判断的标准或提供的判断标准不完备时,就需要由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的过程中来加以设定或补充。这种由行政机关在裁量权行使过程中所设定的作为其依据或理由的判断选择标准,就是我们所谓的“裁量基准”。实际上它是行政机关在具体的个案裁量中对其所依据的理由的一种补充。另一层含义则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所设定的用以确定抽象的个案裁量所普遍适用的标准。它相当于上述“具体化裁量基准观”中所谓的“上级行政机关事先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基准”,也与“规则化裁量基准观”眼中的裁量基准的含义相同。这层含义与前一层含义上使用的裁量基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独立于裁量之外,以规则化的路径而展开的,因而具有特殊的性质功能和独立的研究价值。
尽管上述“规则化裁量基准观”和“具体化裁量基准观”都在这层含义上使用了裁量基准,但是如前所述它们却是分别站在“规则统治”和“说明理由制度”两个不同的立场来认识这种裁量基准的性质和功能。对此,笔者认为,将“规则统治”和“说明理由制度”作为外部控权手段之一种,一直是传统理论的精髓环节,因此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在裁量基准异于传统规范主义控权理论上有所创见,仍旧是一种带有传统的偏见。不过,尽管如此,有学者还是觉察到并隐晦地指出了这类裁量基准本质的特殊性。譬如,依旧留恋传统控权理论的学者往往如此说道——“在肯定以突出裁量基准来控制行政裁量权的实践时,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毕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系统的一种内部控制模式”(注:王建华:《行政裁量控制中的裁量基准和公众参与》,《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除了通过外部的制度作用达到控制目的的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行政权以自我拘束的方式限定空间的制度形式”,而“行政裁量的自我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判例的积累形成的,法院在个案的判决中要求行政机关接受行政惯例或行政机关自身制定的裁量基准的拘束”(注: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毋庸置疑,他们认为裁量基准并不同于上述“说明理由制度”,其可能是控权意志的一种自在自为的发展结果,是行政自我拘束方面的体现。较之上述两种观点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认识上的跨越,它已经不再仅仅集中于外部行政法,而是对裁量基准特有的自我约束气质有所挖掘。
更为深层且值得称道的理论勇气是,现阶段亦有两种另辟蹊径的创见,分别为“软法治理”(注:周佑勇:《在软法与硬法之间:裁量基准效力的法理定位》,《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和“行政自制理论” (注:所谓行政自制,是指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该理论的提出,旨在为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而探求一条新型的行政自我控权路径。参见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它们皆是源于对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扩张理解而出现的系统理论,二者之间最具特色的共同属性在于和司法权彻底断绝了关系。也正因此,在标榜此两种理论的学者眼中,将裁量基准作为获得实践佐证的形式材料是最具说服力的,因为裁量基准实践最早出现于行政机关本身,而非立法机关和理论界,这无疑已是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软法治理和行政自制理论并不尽相同(注:软法理论尽管排斥司法权力的介入,讲求自愿规则,但其更加偏重建立开放式的参与制度,依靠外在权力(主要是社会权力)实施法律控制;而行政自制则更加强调行政主体系统内部的机制运作,譬如公务员内部考核机制、行政权力本身的分化,其和软法监督力量的来源并不相同。),但裁量基准却同时被软法和行政自制论域所囊括,且毫无争辩地被同等解读。当然,这本身并不值得深入辨识。相反,对裁量基准另有价值的是,软法治理和行政自制理论事实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更为切实的解读路径。在它们之中,我们可以确定裁量基准并非必须要在获得司法权的支持之后才能彰显“自我拘束”的异性,其完全可以走向彻底抛弃司法权的康庄大道。
(二)基于实践的观察
上述理论尽管并非只是主观上的空谈,但是仍然需要佐证的是来自裁量基准实践的客观材料。观察各地所推行的裁量基准实践,我们发现,在裁量基准的制度生成中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或显著特色值得关注,一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二是“规则之治”的进路。
首先,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裁量基准进入中国行政法治的视野,最初源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对基层执法的典型经验总结与实践性创造,实际上凝练了地方基层执法者的智慧。这可以从浙江省金华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践予以观察。作为裁量基准实践的先行者,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于2004年2月率先在全国推出了《关于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注:《金华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关于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金市公通字[2004]23号。),由此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制度生成的路径看,金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产生肇始于金华市公安局在2003年4月组织开展的裁量基准试点工作。面对公安执法中比较突出的“执法随意、裁量不公”的问题,金华市公安局要求各县市局和分局选择一至两个治安状况复杂、案件数量较多、执法比较规范的科所队作为试点单位,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再确定一至两种最易滥用处罚裁量权的热点、难点违法行为展开裁量基准试点。(注:参见《金华市公安局关于开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点工作的意见》,金市公字[2003]36号。)在将近一年的试点、总结和完善的基础上,金华市公安局于2004年2月制发了《关于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在全市公安机关全面推开了对赌博、卖淫嫖娼、偷窃、无证驾驶、违反互联网营业场所规定等五种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裁量基准制度在公安系统的成功实践,引起了金华市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得以从2006年开始在全市范围予以推广。(注:参见《金华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意见》,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金政办发[2006]49号。)可见,金华裁量基准的产生所走的是“县级公安局的科所队→市公安局→市政府”的自下而上之路,其制度设计是处在行政执法第一线的基层部门在微观行政执法领域的经验总结和实践创造。显然,在我国作为“自下而上”来自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典型经验,大量裁量基准的制定都是出自基层的市县级行政机关,而并非具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这些由基层行政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只是为裁量权的正当行使提供一种具体化的约束标准,并不能构成一种立法性规则或者法律规范。
其次,在实践中,裁量基准作为“规则之治”的进路甚至过度规则化的倾向,也不容忽视。有人观察认为:“我们发现,这一制度的核心技术,主要是通过‘规则细化’甚至‘量化’的方式而压缩,甚至消灭自由裁量。”(注: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这样一种将裁量基准完全纳入传统规则主义控权模式的解读,或许只是一种“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裁量基准毕竟普遍采取的是事先制定规范性文件或规则的设定方式,带有明显“规则之治”的控权色彩。比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注:2008年4月1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22号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第90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裁量权基准,是指行政机关依职权对法定裁量权具体化的控制规则。” “裁量权基准由享有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制定,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裁量权基准的制定程序,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办理。裁量权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开。” “行政机关应当遵守裁量权基准。” 《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注:2009年11月1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44号公布,自2010年4月17日起施行。)第12条第4款进一步规定:“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适用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注:2009年5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8号公布,自2009年7月4日起施行)第9条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市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后公布实施。”《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注:2011年6月2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38号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第59条规定:“行政执法不得滥用行政裁量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行政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可见,无论从裁量基准制定的主体(一定层级的行政机关)、时机(在具体裁量权行使之前)、形式(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程序(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还是其对内效力等要求来看,实践中都是将其作为一种对裁量权的“规则之治”在进行制度安排和设计。而且,其目的都是“规范”并防止裁量权的滥用。既然如此,完全排除裁量基准作为规则的拘束力也是欠妥的。
(三)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性质定位
基于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实践观察,笔者认为,裁量基准兼具“行政自制”和“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在性质上应当定位为一种裁量性的行政自制规范,或者说是一种自制型的裁量性行政规范。
其一,作为“行政自制”的内在品质。相对于既有的纯粹的规则主义立场而言,行政自制视角更加关注裁量基准的自我控权品质。(注: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行政内部分权》,《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与传统模式存有差异的是,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并不属于法或立法性规则的范畴,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内部行政规则,抑或说是类似于美国行政法理论中的“非立法性规则”(non-legislative rule)(注:Richard J.Pierce,"Distinguishing Legislative Rules from Interpretative Rules",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0,52,pp.552557 )。作为“行政自制”的裁量基准,其至少应保持以下三方面特性:第一,这一控权逻辑的大部分定在形式催生于行政主体自身的执法实践,而非智者抑或是立法者的设计;第二,行政自制偏重于对社会力量的尊重,而非国家权力,且在社会权力监督来源上,更加注重行政主体自身的“道德反思”,或者是自我反省,而非我们在论证传统外部调控机制时提到的“广泛的公众参与”;第三,行政自制尽管与其他权力存有关系,但始终保持一种相对理念,譬如“设定义务的相对性”、“裁量基准的相对公开性”等方面,这是因为,行政自制一方面是对行政权的自我“治理”,另一方面也仅仅是“自我”治理,而非其他。
其二,作为“规则之治”的外在功能。倘若“行政自制规范”仅仅能被解释为行政自制的一半内容,这恰恰又是存在危险的。这样的解释,不仅是对实践中普遍采取规范性文件或规则设定方式的漠视,而且无法与既已存在的软法治理与行政自制理论加以区分。(注:在某种意义上,软法治理与行政自制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控权理论,正因如此,其在日渐兴起的同时,也因陷入主观主义而遭到了批判。参见魏武:《冗余的软法》,《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规则之治”与“行政自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体现在裁量基准的表现形式和外在功能上,而后者则更多关注的是其内在的控权逻辑。“规则之治”的具体要求是裁量基准的设定必须根据授权法的旨意,这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立法目的、法律原则。这种限制的目的在于,其能够保证裁量基准的设定只是法律对裁量权约束的一种延续。但是,对裁量基准属性定位具有较多影响的依旧是其中的“行政自制”成分,而并非“规则之治”,因为裁量基准毕竟在控权逻辑上与传统或者纯粹的“规则化”立法控制存有差异。
(四)技术、形式与功能的结合
基于对裁量基准的性质定位,具体可以对其作出这样的界定:所谓“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授权法的旨意,对法定授权范围内的裁量权予以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而事先以规则的形式设定的一种具体化的判断选择标准,其目的在于对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形成一种法定的自我约束。根据这一界定,对裁量基准的理解,必须将技术、形式与功能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把握它在这三个层面的法律属性。
1. 技术上的“裁量性”。裁量基准使用的技术是“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来回穿梭’,是法律适用的普遍特征。”(注:[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尽管行政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产生的法律效果作出处理决定的权力,只存在于法律效果的处理之中,但是任何裁量决定都必然涉及对各种事实情节的综合考量,并建立在权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其实质是一个复杂的利益衡量过程。对事实要件的认定,为对处理决定的裁量奠定了基础。(注:参见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第16页。)而在个案裁量中,这种对“事实要件的认定”反映在法律规范之“要件—效果”结构中,也就是对“法律要件的判断补充”。从这种意义上讲,行政裁量就是行政机关在对法律要件作出判断补充后对法律效果所作出的适当选择,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裁量=要件判断+效果选择。因此,任何一个裁量基准的设定,并不是单纯对法律效果的格次化,也包含着对引起该效果的事实情节的细化,两者共同构成了裁量基准对裁量规范中的“事实—效果”规定的一种完整补充。
例如,《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注:2005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8号发布,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第36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损坏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的……”针对这一规定,《南京市城市客运管理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注:宁公法字[2006]246号。)设定如下“细则”:
1.损坏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造成轻微损失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2.损坏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造成车辆停驶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五百元以上两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3.损坏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造成线路中断运行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两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这一“细则”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规定的“损坏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的”这一事实要件细化为“造成轻微损失的”、“造成车辆停驶的”、“造成线路中断运行的”三种不同情节,并将前者规定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裁量范围格化为“5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1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2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成为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判断标准,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裁量基准。
从裁量基准所使用的“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这两种技术来看,裁量基准实质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与具体个案裁量中的利益衡量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根据作为利益载体的情节的轻重来选择不同的法律效果。在这里,它既没有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也没有采取纯粹法律解释的方法,而是使用了一种利益衡量的方法,因此不能归属为立法性规则,也不完全就是一种解释性规则,可以称之为一种“裁量性”行政规则。
2. 形式上的“规则性”。裁量基准以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性质上并不属于法或者立法性规则的范畴,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一种内部行政规则。法或者立法性规则必须创设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具有普遍法律效力并为司法所统一适用。在我国,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法源地位的立法性规则仅限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法定解释性行政规范。(注:法定解释性行政规范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解释。《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的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3条规定,“规章的解释同规章具有同等效力”。)而裁量基准主要是通过对裁量权规范的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的技术,补充裁量权的判断标准,并不为相对人创设权利和义务(注: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4条关于“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的规定,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裁量基准也无权为不特定相对人创设有关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不对相对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也不构成一种裁判性规范,不能为司法所直接适用。尽管裁量基准也可以通过其体现出的法律原则并在个案的反复适用中形成一种行政惯例而获得一种间接的法律效力,但是在承认行政惯例和法律原则具有司法适用效力并作为裁量基准的效力依据的前提下,作为行政规则的裁量基准本身也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仅仅是行政惯例和法律原则的载体,因此并不直接构成对法院审判具有强制性和拘束力的依据。(注:参见周佑勇:《在软法与硬法之间:裁量基准效力的法理定位》,《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
然而,行政裁量基准毕竟是以一种规范性文件或规则的形式而存在的,在性质上又应当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制定的一种行政规则。“任何行政官员只要拥有裁量权,就必定拥有公开说明如何行使相关裁量的权力,而不管立法机关是否单独赋予该官员制定规则的权力”(注: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1,p 68 ),因此,设定裁量基准的权力源于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它与裁量权的授予相伴而无须单独授予。但是,裁量基准一旦制定出来,它的实施则依赖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一种层级指挥监督权。正是基于这种内部层级指挥监督权,裁量基准具有一种对内的拘束力,以保证其在行政系统内部得以贯彻执行,并成为一种自我拘束的内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自我拘束机制,无论是它的设定还是运行都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体现的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纵向科层制管理。
当然,行政机关制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的行政规则即行政规范,通常包括创制性行政规范、解释性行政规范和指导性行政规范三类。(注:参见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以下。)但是裁量基准并不属于这三类之列,而是一种独立的“裁量性行政规范”。首先,创制性行政规范是根据明确的立法授权,为相对人创设了权利义务,具有法律拘束效果的规则,其在功能上等同于立法性规则或法律规范,因而裁量基准不应当是创制性行政规范。其次,裁量基准也不是指导性行政规范。指导性规范是对法律规范所作规定的具体化,没有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众多裁量基准的名称中可能被冠以“裁量指导意见”、“裁量参照标准”等称谓,但实际上裁量基准并不是非强制性地、依靠相对人自愿的配合而获得实施。相反,对内,它以行政权威为基础、以执法考评和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为辅助,对下级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具有强行性效力;对外,“通过行政机关的适用,行政规则具有事实上的外部效果”(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即对于外部相对人也具有一种间接的法律拘束效力。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裁量基准在法律属性上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解释性规范。(注:参见朱新力主编:《法治社会与行政裁量的基本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的确,裁量基准在内容上是对法律条文的细化和分解,目的在于约束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和执行,与解释性行政规范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但是笔者认为,裁量基准有着重要的特殊性,这些特性使其区别于解释性行政规范,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规范即“裁量性行政规范”。裁量性行政规范和解释性行政规范的区别(注:实际上,德日行政法学中已有这两个概念的界分。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将行政规则分为组织和业务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性规则和替代性规则四类,日本学者盐野宏在对“行政机关的行动基准”的分类中亦存在解释基准和裁量基准的区分。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593页以下;[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制定目的上,解释性行政规范是法律条文含义的具体阐明和确定,旨在消除误解和分歧,统一适用者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而裁量性行政规范虽然也是对法律条文的具体化,但并不是基于词义理解上的模糊性,而是出于操作空间上的宽泛性,目的在于限定执法者的裁量空间,约束和规范裁量权的行使。其次,在规制技术上,解释性行政规范采用的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其技术的核心在于探寻和遵循能指与所指、表达与意图等语义上和体系上的逻辑联系;而裁量性行政规范所运用的是“情节的细化技术”和“效果的格化技术”,至于如何细化和格化、处罚格次是分成三格还是四格,并不是取决于语义逻辑,更多地在于制定基准的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和政策考量。最后,在审查标准上,对于解释性行政规范,作为法律专家的法院应具有完全审查决定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正确与否的最终权力,即适用全面审查的标准;而裁量性行政规范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法院应予以适度的尊重,一般只审查其合法性,即适用有限审查的标准。由此可见,裁量基准在学理上应该更为准确地定性为裁量性行政规范,而非解释性行政规范。
当然,“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这两个概念在实践中往往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分离”(注:王天华:《裁量基准基本理论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裁量基准中经常会包含属于解释性行政规范的内容和要素。尤其是“情节的细化”往往就是对“法律要件”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种解释,构成一种解释性规范或解释基准。但是,设定裁量基准的方式是进行“要件—效果”的补充规定,除了“情节的细化”外,还必须有“效果的格化”与之相对应,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裁量基准。而且如前所述,这样一个根据各种细化后的情节进行“效果格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而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解释过程。因此,即便是裁量基准的“情节细化”构成一种解释性规范或解释基准,也并不影响裁量基准与解释性行政规范的区分,以及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裁量性行政规范的整体定性。
3. 功能上的“自制性”。从表面上看,行政机关设定裁量基准只是为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一种具体的判断选择标准,但是如果欠缺这种标准,就可能导致裁量权的滥用或不当。因此,裁量基准的设定并非纯粹为了“通过‘规则细化’甚至‘量化’的方式而压缩、甚至消灭自由裁量”(注: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其内在目的在于保证裁量权的正当行使,或者说对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形成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规制”,在功能上具有“自制性”。
当然,裁量基准的这种“自我约束”仍然体现的是一种“法的约束”。只不过这种“法的约束”主要来自授权法的旨意,包括立法的目的和基本的法律原则。比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2条规定,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应当根据“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立法目的、法律原则”。裁量基准受到“法的约束”,实际上意味着整个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也就受到了法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裁量基准的设定只是法律对裁量权约束的一种继续。对裁量权的法律约束而言,尽管法的外部约束已经停止,但是法的内部约束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这种“法的约束”通过裁量基准的形式延伸到裁量权的整个判断选择过程之中,从而使裁量基准成为连接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个案裁量之间的桥梁,既是对抽象的法律具体化,又为下一步针对个案作出具体裁量决定提供一般化的行为模式,由此而具有沟通抽象性法律与个案裁量之特殊的结构功能优势。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法律属性可以看出,裁量基准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之治”,并不同于纯粹“规则化”的立法控制。虽然裁量基准本身是一种“规则”,但绝不同于“规则主义”中所表达的“规则”。严格意义上说,“规则主义”是一种利用外部力量规制权力的路径,而裁量基准仅仅是内部控权技术,不仅功能上表现为“自制”,且制定技术上也不同于传统的“立法”技术。因此,“裁量基准”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控权理论的特殊“规则之治”。从根本上说,裁量基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裁量性行政自制规范或自制型的裁量性行政规则,是行政机关对裁量权行使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制的一种制度创新。
(五)对裁量权的限定、建构与制约功能
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裁量性的行政自制规范,主要是通过诉诸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的裁量技术而体现出对裁量权的限定、建构与制约功能,从而具体实现其对裁量权行使的自我控制功能。
1. 对裁量权的限定。裁量正义的精髓在于剔除那些不必要的裁量权,并对必要的裁量权加以规范和控制。否则,都有可能导致裁量权的恣意和滥用。针对裁量太宽或过度的问题,通常需要立法机关穷尽一切法律细节来详细地确定所授出裁量权的范围,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已被实践证明往往很难实现。这就需要行政机关将法定授权范围内的裁量权进一步限定在一定界限范围内。裁量基准作为一种确定裁量权行使标准的行政规则,通过诉诸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这两种技术,使模糊的立法标准明确化,使宽泛的裁量权范围具体化,从而达到对裁量权的限定。譬如,前述《南京市客运处罚裁量规则》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所规定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这一宽泛的裁量范围格化为“5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1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2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三个处罚格次。这样,裁量基准通过对处罚的格化,在法定的裁量范围内进一步确定了裁量权行使的界限,明细了不同的裁量空间,从而发挥着对裁量权的限定功能。
2 .对裁量权的建构。对裁量权的限定旨在剔除那些不必要的裁量权,以保证裁量权不超越规定的界限,但是对于必要的裁量权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控制,以保证裁量权在界限范围内的正当行使。这就涉及对裁量权的建构。“无论是对裁量权的限定还是建构,行政规则的制定都是一项尤为重要的工具,其中确立裁量权界限的规则是对它的限定,而对行政官员在界限内如何行使裁量权加以具体化的规则就是对裁量权的建构。”(注: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1,p 97 )这种对裁量权的建构功能主要通过裁量情节的细化技术体现出来。作为处罚格化的基础和依据,情节的细化使得裁量格次的划分更加合理、科学又具有可操作性。而无论何种情节,都属于对裁量个案中的利益衡量与处理决定具有直接影响和作用的各种事实情况,是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全面考虑的因素,对与之无关的因素则不得予以考虑。否则,就属于“不相关考虑”而有悖于立法授权的真实意图,从而导致行政裁量权行使的违法或不当。裁量基准通过诉诸情节的细化技术,确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应当综合、全面考虑的各项要素,以及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从而保证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实现对裁量权实体内容的有效建构。譬如,前述《南京市客运处罚裁量规则》将处罚的情节根据危害后果细化为“造成轻微损失的”、“造成车辆停驶的”、“造成线路中断运行的”三种不同情节。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个案裁量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三种要素,来选择不同的罚款金额。而这三种要素是在与相应的处罚格次进行充分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可以确保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3. 对裁量权的制约。裁量基准通过诉诸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技术,事实上公开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判断过程。而公开是专断的天敌,“是对抗裁量权专断行使的最有效武器”(注:Kenneth Culp Davis,Discretionary Justic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1,p 111 )。公开不仅能够保证裁量基准对裁量权的建构功能得以发生完全的效果,也为对裁量权的制约提供了保障措施。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裁量基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过程就被封闭于‘暗箱’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审查)、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乃至权利对权力(私人对行政)的监督都会缺少必要的信息来源。” (注: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此外,虽然相对于来自行政系统之外的立法和司法控制而言,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但是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视角下,它则更多地带有“他律”的分权制约色彩。譬如,作为裁量基准制定者的法制部门与具体执法者之间,上级行政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之间,体现出了行政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之间的分离与制约。在此前提之下,裁量基准对于具体执法者和下级行政机关来说,实际上就是来自裁量基准制定者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的“他律”控制了。
上述可见,通过诉诸裁量基准对裁量权行使的自我控制,可以发挥对裁量权的限定、建构和制约等三个方面的功能作用。而在这三个方面均可以加上“自我”的修饰词,即对裁量权行使的自我限定、自我建构与自我制约,由此彰显出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规范对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控制功能。此外,在其中,“限定”只是为“建构”提供前提,“制约”则是为“建构”提供保障,裁量基准的核心功能应当在于自我建构,且是一种主动、内发,能动、积极的建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注:所谓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是相对于传统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而言的一种重要的裁量治理模式。它强调的是一种行政的自我治理,即通过行政裁量运行系统内部各种功能要素的自我合理建构,来充分展现其固有的能动性和实现个案正义的内在品质。参见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立场》,第41页。)。
二、行政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基础
基于回应变化多端的行政事务难免带有仓促,公法学理论往往需要一个逻辑假设的支撑——或是正当性基础,或是合法性基础,其目的旨在彰显理论关怀的同时又不至于脱离宪政的整体框架。透过裁量基准的实践,其存在的价值和现实功能已经毋庸置疑。然而,符合经验的并不一定就符合理性。裁量基准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自制规范,能否在一国宪政框架中获得接纳,仍然需要对其存在的正当性加以理性的追问。不仅如此,它将作为逻辑前提直接决定裁量基准各种制度细节的走向。然而,在时下有关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中,“裁量基准具有正当性基础”这一逻辑假设仍然只是假设,而并未获得理论上的确证。与之相反的是,理论界对裁量基准存在的正当性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否定态度,并由此给实践认识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亟待对此加以检讨并作出合理的回应。
(一)来自理论上的质疑及其消极影响
理论界对裁量基准的正当性质疑,主要表现为“权力来源的违法性”与“控权逻辑的无效性”两方面:
1. 权力来源的违法性。首先,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一定层级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拥有行政立法权(注:根据《立法法》第56条、第71条和第73条的规定,具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都享有这一权力。据此有学者认为,不享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裁量基准是具有合法性瑕疵的。(注:参见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其次,在裁量基准的作用力层面,由于现阶段理论研究并不否认裁量基准的法律拘束力,尤其是其外部法律效力(注:See Peter Strauss,"The Rulemaking Continuum", Duke Law Journal ,1992,41,p.1463。),因而当某项裁量基准的文本内容涉及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益时,其在宪政框架内的正当性确证问题便得以凸显。而由于我国《立法法》第8条已经设置了类似德国《基本法》的“法律保留”条款(注: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研究》,《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应松年:《〈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因而当实践中出现某些涉及相对人人身与财产权益的处罚基准时,便有违《立法法》第8条的宪政精神。
2. 控权逻辑的无效性。除了来自规范主义层面的质疑外,还有观察者认为,即使是将裁量基准置于功能主义视野中予以检讨,事实上其控权逻辑的有效性依旧有待商榷:其一,对裁量基准的严格适用,会在满足形式平等的同时,对实质平等有所损害。僵化的规则限制会将行政执法应有的行政正义逐渐推向消亡,执法实践所需要的个案正义亦会招致裁量基准的违法性谴责。“由于参与的变量过少,使得裁量过程过于简约,(裁量基准)未必总能反映客观实际、实现个案正义”(注: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因此,在宏观层面,裁量基准事实上背离了时下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变换的时代背景,因而其在控权逻辑上并不具有正当性。(注:参见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其二,在技术层面上,裁量基准也并不是一种可以大规模推广的控权技术,其实际功效与舆论的热烈程度是没有关联的,其本身存在“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规则足够细化尽管会达成控制裁量权之目标,但也会导致裁量僵化;反之,如若留有范围,依旧会有裁量空间残存,这又必将与控权目标有所偏离。(注:参见崔卓兰、刘福元:《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规则化》,《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因此,催生于执法实践经验的裁量基准,既没有批发生产基准文本的主体能力,也不可能以此而达成完全意义上的作茧自缚。
上述质疑的整体影响在于,无论是在规范主义论域中考量裁量基准的权力来源,还是从功能主义立场检讨裁量基准的制度功效,其正当性基础都不具有尘埃落定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乎正当性基础的不确定态度已经以一种令人担忧的形式延伸到了实践推广中,且引起了实践认识的模棱两可与非理性。具体表现为:
1 .尽管国务院在2008年公布的《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和2010年公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都明确对裁量基准制度表示了肯定,但时至今日,国务院拟出台的《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我们并不十分确定寓于其中的个中缘由,但上述有关裁量基准正当性基础的检讨以及得出的否定性结论,可能是其因素之一。
2. 更为明显的例证是,在该《意见》中,一项有关裁量基准制定主体的制度安排则直接表达了其否定态度。该意见稿提及:“适用规则的制定主体是各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已经制定适用规则,与省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适用规则有不一致的,应当进行修订;省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适用规则不一致的,同为规章的,依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同为规范性文件的,可以优先执行省级政府制定的适用规则。”(注:李立:《我国将统一规制行政裁量权,适用规则权收归省部级》,《法制日报》2009年10月20日。)这一被学者理解为“为了防止行政执法出现十里不同天”(注:章志远:《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2期。)的绝对平等主义的立法思路,尽管已经被冠以“非理性”的评价(注:如有学者指出,“该思路漠视了个案裁量中地方性知识的存在”(章志远:《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2期);“如果提升裁量基准制定主体的层级,将使裁量基准的经验合理性大打折扣”(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但我们应当看到,其为了避免裁量基准制定主体合法性瑕疵的良苦用心,却是不言而喻的。在渊源上,这与上述理论界对裁量基准主体合法性的否定性评价不无关系。同时,与对裁量基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担忧相关联的是,各地对待裁量基准制定主体的处理方式亦存在着极大混乱。譬如,2009年《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第1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都有权制定裁量基准,但是2011年《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10条却将有权制定裁量基准的主体确定为“省人民政府或者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所属行政处罚实施机关”。
3. 在司法审查问题上,基于欠缺正当性确证,国内行政诉讼在面对裁量基准时往往欠缺最为基本的准则,而这最终亦将影响到裁量基准的制度成长。譬如,在备受学界关注的“周文明诉文山交警不按红头文件行政处罚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便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裁判结论,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所涉及的红头文件具有拘束力,行政机关理应遵守,但二审法院却持相反态度。(注:参见陈娟:《驾驶机动车超速,究竟罚多少:云南省公安厅红头文件引争议》,《人民日报》2008年4月2日。)当然,这可能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内容存有关联,但我们也应看到,倘若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基础已经获得确证,法院对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便理所当然需要给予最为基本的尊重。(注:“政策性、技术性越强,司法越应谦抑。”王贵松:《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因此,这依然可以归为一种由质疑正当性基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可见,意欲谋求裁量基准制度的进一步推进,我们无法回避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基础问题,必须消解来自“权力来源合法性”和“控权逻辑有效性”方面的质疑。否则,基于正当性担忧,诸如上述《意见》中的非理性制度安排便会涉足其中,而担忧之后所产生的规范混乱,也将会导致与裁量基准的制度初衷日渐背离。 然而,在逻辑上,通过制度细节一一予以回应,肯定无法穷尽所有问题。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我们对裁量基准的基本属性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或者遗漏,那种仅将裁量基准定性为“规则统治”的片面认识,给正当性基础所能带来的只能是片面判断,其为制度实践所能带来的也只是片面理解。因此,对正当性质疑的根本性回应,必须追溯到裁量基准的属性定位上。
根据前文关于裁量基准的性质定位,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裁量性的行政自制规范,是一种兼具“规则之治”和“行政自制”双重品质的新型控权技术。由此必须站在规则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双重立场上去解决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其一,在规则主义立场上,形式上体现为“规则之治”的裁量基准,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其二,在功能主义立场上,功能上体现为“行政自制”的裁量基准,其控权逻辑的有效性问题。
(二)裁量基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尽管与纯粹的规则主义有所差异,但在外表上还是呈现出了“规则之治”的形式特征,其实质就是一种立法性裁量权或规则制定权的运用,“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制定法律”(注: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p 70 )。然而,按照西方古典意义的宪政分权理论,立法权专属于立法机关行使,非经立法机关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得为任何立法性事项,以限制政府通过立法手段谋求行政权力扩张的正当性,防止行政机关未经授权对私人自治领域的侵入。这种限制性授权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以法律保留为核心,在英美法系国家则直接表述为“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或“禁止授权原则”。在我国,《立法法》第8条也设计了类似的法律保留条款。因此,倘若从规则主义角度将裁量基准定性为一种立法性裁量权或规则制定权的运用,则理所当然需要对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加以检讨。只有冲破作为限制性授权理论的“法律保留原则”和“禁止授权原则”的禁区,裁量基准才能获得其在宪政框架下生存的正当性基础。
1 .基于比较法上的考察。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制定类似于我国裁量基准这样的行政规则来实现对裁量权的自我约束,在国外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其表现形式包括规则、指南、指令、标准、准则、备忘录、信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务员手册以及培训材料等多种多样。(注:See Lorne Sossin and Charles W.Smith,“Hard Choices and Soft Law:Ethical Codes, Policy Guidelines and the Role of the Courts in Regulating Government”,40 Alberta L.Rev .867, 871(2003).)这些裁量基准的各种形式,在法国法上被概称为“指示制度”(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或“指示”(注:[法]让·里韦罗、让·瓦利纳:《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98页。);在德国和日本法上,被归属于“行政规则”(注:黄舒凡:《行政命令》,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23页。);在美国法上,则被归属于“非立法性规则”(non-legislative rule)(注:Michael Asimow,"Nonlegislative Rulemaking and Regulatory Reform", Duke Law Journal ,1985, 381,p.426 )或“解释性规则”(interpretative rule)(注:Richard J.Pierce,"Distinguishing Legislative Rules from Interpretative Rules",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 2000, 52, pp.552557 )。基于比较法上的考察,在西方公法史中,行政机关制定的这些类似于裁量基准的行政规则能够在现行宪政框架中获得生存,都经历了一个是否有违“法律保留原则”或“禁止授权原则”的正当性争议。
按照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奉行的法律保留原则,特定范围之内的行政事项专属于立法者规范,行政非有法律授权不得为之,否则将会受到违宪的指责。(注: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52页;苏嘉宏、洪荣彬:《行政法概要》,永然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7页;[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104页。)该原则是19世纪奥托·迈耶在君主立宪的背景下作为宪政主义的宪政工具而发展起来的,其初衷是在三权分立原则下,严格限定立法与行政两权的权限分配秩序,尤其是使立法权能够足以对抗行政权的边界侵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行政权力急剧扩张而立法机关的立法职能相对弱化,有关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随之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对传统的限制性授权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4年“导弹部署案”中采纳了欧森布尔等人倡导的“功能结构取向方法”来重新解释法律保留的宪法理论依据,认为:“权力的区分与不同功能配置不同机关,其主要目的无非在于要求国家决定能够达到‘尽可能正确’的境地,换言之,即要求国家的决定应由在内部结构、组成方式、功能与决定程序等各方面均具备最佳条件的机关来担当作成。” (注:许宗力:《论法律保留原则》,《法与国家权力》(一),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立法权固然具有多元民主基础、烦琐、审慎及公开、透明决定程序等功能因素,导出重要国家事务仅能由立法者以法律规定,才能达成“尽可能正确”结果,进而证成法律保留原则;然而,行政权也能根据行政之专业、灵活、弹性、快速、效率等功能因素,导出特定事项无须法律之授权,由行政自行以命令规范,反更能达到“尽可能正确”之境地的结论,从而证成职权命令合宪的存在。(注:参见许宗力:《职权命令是否还有明天?——论职权命令的合宪性及其适用范围》,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46—347页;盛子龙:《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之司法审查密度》,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4页以下。)按照这种解释,凡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应有法律授权的依据,凡不在法律保留范围内之事项则存在职权命令的空间,即行政机关可以无须法律授权而自行依法定职权制定命令规范。由此上级行政机关凭借其指挥监督权为下级机关制定作为行政规则的裁量基准,就获得了合宪性依据。相应的,在德国行政法上,出现了侵害保留、全部保留、重要性保留、国会保留等学说。(注: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第189—191页。)尤其是重要性保留理论的提出,为作为职权命令的裁量基准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和正当性基础。
同时,为了提供更为彻底的理论基础,德国学者还曾于法律保留原则的另外一端另辟蹊径,创生了类似的“行政保留”学说。行政保留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权力分立的基础上尊重和保障行政权的应有空间,这一空间是指“具有宪法效力的、避免国会干涉的、行政权得自己形成的领域”(注:林锡尧:《行政法要义》,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6页。)。持行政保留者认为,我们应对行政力所能及之权限范围予以尊重,因为“行政权自主地位之丧失,不仅与权力分立之精神相违背,与国家职能运作之实际情形亦不相符,且真正落实基本权利之保障者,主要依赖行政部门之具体措施,而非立法或司法部门”(注: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行政保留的范围包括“执行法律权”、“组织权”、“行政的规范制定权”及“行政的补充权”等事项(注:参见廖元豪:《论我国宪法上之“行政保留”——以行政立法两权关系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2000年第1期。),这其中所谓的“行政的规范制定权”作为行政机关特有的保留空间,能够为裁量基准的正当性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撑。
与大陆法系国家注重法律保留的理论传统相对应,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行政法的传统模式则是直接通过“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对立法性裁量权加以控制。该原理的前提性信念是基于“被授予的权力不能授出”这一法的普遍原则。(注: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根据这一原理,立法机关所拥有的立法权是宪法授予的,它不能将该项权力再次授予任何其他人或其他机关。(注:See Kischet,"Deleg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 to Agenc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 Law",46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16(1994) )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必须精确地表述其给予行政机关的指令,而不得授予其立法性的裁量权力。在早期的美国法律发展过程中,“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作为一种最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支持。首次明白宣称根据分权原则立法权力不能授出的案件是1892年的菲尔德诉克拉克案(Field v.Clark)。在该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认为授予总统改变进口关税税率的权力是行政性的裁量权而非立法性的裁量权,但同时声称“国会不能将立法权授予总统,这是一项被公认的原则,它对维护依宪法而成立的政府系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注:Field v.Clark, 143 U.S.649 (1892) )。而在1935年的巴拿马炼油公司案(Panama Refining Co.v.Ryan)和谢克特家禽案(Schechter Poultry Corp.v.US)两案中,法院则以法律授权缺乏合适标准、范围过宽为由,分别判决国会的相应授权违宪而无效。(注:See Panama Refining Co.v.Ryan,293 U.S.388(1935);Schechter Poultry Corp.v.US,295 U.S.495(1935) )但是,自1935年以后,由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行政事务的不断扩张,国会不得不广泛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性权力。法院虽然继续承认传统的“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但除涉及人身自由等问题外,从未严格检查授权法中的标准或原则,也从未否认授权法的效力(注: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禁止授权原则似乎已经死了(demise)。(注:See Andrew J.Ziaja,"Hot Oil and Hot Air: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delegation Doctrine through the New Deal, A History,18131944",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2008,35,p.925 )特别是在2001年的惠特曼诉美国卡车联合会案(Whitman v.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中,法院明确指出:“我们的回应不是去否定法律,而是给管制机构一个自行演绎出确定标准的机会。”(注:Whitman v.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 531 U.S.457(2001) )这意味着美国传统立法授权理论的重要变化,即面对现代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法院不应当仅仅注重要求国会为授权立法规定明确的标准,转而应当要求行政机关自行制定具体标准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拘束。(注:See Cass R.Sunstein,"Nondelegation Canons",67 U.Chi.L.Rev .316 (2000) )
实际上,自1984年的“谢弗林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Chevron USA v.Natural Resource Defense Council )以来,法院一直保持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各种解释性规则的尊重,只不过司法尊重的程度不同而已。(注:参见[美]史蒂文·J·卡恩:《行政法:原理与案例》,张梦中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359页。)现在,这一尊重态度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成长为一种标准,譬如“谢弗林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确立的“谢弗林遵从”标准(注:See 467 U.S.837(1984).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法律解释,只要合理,均应予以尊重。因此“谢弗林遵从”所确立的是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一种高度尊重。See Lindsay J.Nichols,"The NMFSs National Standard Guidelines:Why Judicial Deference May Be Inevitable",91 Calif.L.Rev .1375 (2003).),Christensen v.Harris County案(注:529 U.S.576(2000) )和United States v.Mead Corp案(注:533 U.S.218(2001)))中确立的“斯基德莫遵从”标准等等。如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有关区分行政、司法、立法之间权力界限的裁判中,均需考虑此类标准。对行政机关给予司法尊重,除了行政机关拥有专家知识的技术优势和较之法院更强的民主化决策程度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权本身就伴随着裁量权的授予(注: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p 68 ),即在法律将某个方面的裁量权授予行政机关时,行政机关就有权依据国会授权作出相应的解释性裁量基准,而无须国会单独授予。可见,在美国,通过司法判例对国会授权的重新解释,逐步冲破了“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的禁区,从而使行政机关事实上拥有广泛的立法性裁量权。裁量基准作为一种立法性裁量权的运用,在美国宪政体系中也由此获得了应有的正当性基础。
2 .在我国宪政体制中的确证。基于上述比较法的视角,域外对裁量基准合法性问题的处理,是伴随行政国家的日益扩张而逐渐折中的。其中,不仅有传统理论的消退,同时亦有来自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大胆拓新,而正是基于这一调试历程的磨合,作为非立法性规则的裁量基准才得以摆脱权力来源的质疑与非难。在我国,亦存在着能够起到阻碍作用的、类似于德国法律保留原则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因此对裁量基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确证,最终还需要在我国宪政体制中加以检讨。
需要在规范层面加以区分的是,域外有关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阻碍通常是因为宪法明确将立法权仅授予国会或议会机关,而并不规定行政机关享有立法权。譬如,在德国,基于法律保留原则而产生的对裁量基准的是非争议,是因为德国《基本法》第80条规定:“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州政府可经法律授权颁布行政法规”,该条中“可经法律授权颁布行政法规”意味着德国《基本法》并不承认“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州政府”享有立法权,其只有经过授权才能获得立法权。又如,在美国,有关禁止授权立法的争议源头则在于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1项规定:“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均属于参议院与众议院所组成的美国国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上述宪法规范是对行政立法权的直接否定,其导致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往往会受到违宪方面的质疑,产生上述各种理论争议的根源正在于此,而并非“法律保留”条款本身。
但是,与上述不同的是,我国宪法对行政立法权直接作出了肯定性规定。譬如,《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第10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也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等等。因此,在我国,行政立法权并不涉嫌违宪。究其根源,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政体制,而并非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因此并不存在上述“禁止授予立法权”问题的障碍。按照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拥有全部权力,而是由宪法设定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享有并行使各自不同的职权。(注:参见邓世豹:《授权立法的法理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宪法并没有将立法权专属于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是直接授予了政府的立法权和规则制定权。所以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都有权制定不同效力层级的行政规则。这些行政规则既包括解释性的规则,也包括创制性的规则和指导性的规则(注:参见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自然也包括裁量基准这类裁量性规则。可见,无论在宪法的规范层面还是现行宪政框架内,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规则而存在均具有正当性的根据。
当然,尽管我国现有宪政体制并不否认裁量基准这类行政规则制定权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作为合法形态而存在。对此,我国《立法法》第8条事实上亦起到了阻碍行政立法权过度扩张的制度功效,其往往被称为类似德国的“法律保留”条款。《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就形式而言,这或许是我国宪政体系能够阻碍裁量基准正当性的唯一依据。但是我们认为,《立法法》第8条仅能作为裁量基准是否合法的边界或立法性控制,而不能据此否认裁量基准权力来源应有的合法性空间。这是因为:其一,如上所述,否定合法性的路径理应是从宪法规范中找到立法权专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条款,此条款非但在我国《宪法》中并不存在,相反,我国《宪法》第89条第1项和第107条都明文规定了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立法权。其二,我国执法实践中的裁量基准并没有创设权利与义务,行政机关只是在其裁量权范围之内对法律予以细化,一般而言并不会超出上位法所赋予的权力空间,更加不会侵犯《立法法》第8条的禁止事项。何况该条所确立的法律保留主要是一种“重要保留”,即只有涉及国家主权、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和财产及重要权利等事项才为立法机关所“法律保留”。凡是不在该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行政机关都可以依法定职权制定各类行政规则。因此,大量具有行政规则性质的裁量基准的出台,并不在《立法法》第8条的禁止范围之内,并非都要求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特别的法律授权,它作为一种职权命令亦属合宪性机制。
(三)裁量基准控权逻辑的有效性
依据前述理解,裁量基准尽管首先在形式上具有规则主义的表征,但这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真正主导裁量基准异于传统控权逻辑的特别因素,实际上是其异于传统的行政自制属性。然而,现行行政自制理论倡导与能够起到横向监督功效的国家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彻底断绝关联,由此使其理论本身的有效性或合理性成为一项软肋。因此,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除了需要满足权力来源合法之外,亦需通过行政自制理论的合理性证明,使其获得控权逻辑的有效性。
1. 行政自制的合理性证明。很显然,当裁量基准的控权逻辑在功能主义立场上被作为行政自制加以解读时,其正当性基础内涵便需做相应变更。这是因为,此时裁量基准只是运行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自律机制,而并不与其他国家权力发生冲突。按照行政自制的理解,裁量基准的效力只具有相对性,其效力来源不会从国家权力层面发生。同时,裁量基准对相对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限定为相对含义,因为其并不是直接为了增强社会秩序,而只是想对行政裁量权进行适度压缩。换句话说,裁量基准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行政主体,而非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对裁量基准的理解更多地偏向“权利”的含义,而非“义务”,这其实就是一种相对性,只不过我们习惯于将它标示为“间接效力”而已。因此,此时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已经不需要澄清其如何能够从宪政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基于“间接效力”的裁量基准本身并不会发生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制度作用,也不会为相对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拘束。但问题是,此处和作为规则之治的裁量基准的假设一样,我们假定了行政自制必然是可行的或是能够实现的,而并未追问行政权是否具有“向善”的可能。任何权力事实上都有滥用的天然属性,“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注:[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第248页。)。如此,设定裁量基准的行政机关何以会“作茧自缚”呢?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其能够“独善其身”呢?这无疑有待澄清。对此,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证成“行政自制”何以能够实现,从而确立运用行政自制理论解读裁量基准的前提的合理性。
在理论支撑上,行政自制的正当性可以从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多重角度获得认可。譬如,运用社会学家查尔斯·霍恩·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理论(注:参见[美]查尔斯·霍恩·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便能揭示出政府亦是运转于行政相对人包围之中的,其亦需获得相对人的价值评判。相应的,政府必须对此评判予以考量并作出调整从而达成相对人的要求,而在此种考量之后所采取的调整方式中,便有行政自制的存在。同时,伦理学范畴中对道德所具备的潜在力量的重视,亦能为从公务人员的道德情操中寻找“自律”提供理论依据。在逻辑上,公务人员自律行为的终极影响是发生在行政机关这一组织体上的,因此,与法律有所区别的公务人员固有的道德情操事实上保障了行政自制并非纸上谈兵,“当人们怀疑行政自制不可能、怀疑行政权不可能内敛或者向善时,是夸张了行政的‘恶’并因此蔑视行政组织及其行政权的存在和功能,这是人们经验观察误区造成的结果”(注: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更具本土特色的文化因素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始原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我们理应将其从人的本性中引导出来,而在总体上将人从善本性引导出来的过程就是“内圣”的过程。同时,“内圣外王”又是中国始原思想中行政官员的必备要素,且“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在中国古代是不需要任何来自外界的控制的,其形成了庞大的道德体系,但却没有设计出一个外部的实体结构来制衡行政官员的权力。(注: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探索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因此,在文化层面,我们亦存有行政自制的文化传统,在我国实行类似裁量基准的行政自制方式,自当不会遭遇本土法律文化的抵牾。
不过,依旧存有质疑的是,倘若按照上述理论推演,行政自制最终可能会落入德治的诘难之中,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权力滥用似乎并不逊于当下,如此我们何以能够牵强附会?又如何能够凭借道德抵制行政专断呢?可见,行政自制控权逻辑的有效性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类推和相互佐证,其亦需在政治层面加以检讨,否则,完全特立独行的行政自制必将陷入德治的圈套。对此,笔者认为,行政自制合理程度的达成与否,至少需要满足应有的民主正当性,且需有相应的外部行政法保驾护航,否则,这一切便只是理论上的空想。
首先,归于行政自制规范范畴下的裁量基准,事实上并没有脱离外部行政法的羁绊。“以宪政思想为基础,外部行政法通过授权立法、司法审查等制度途径为行政自制提供了外部压力和外部管道空间,外部行政法成为行政自制不可或缺的框架。”(注: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在技术上,裁量基准一般而言只是在上位法设定的裁量范围内发挥自制的功能,并不为行政相对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其效力也仅仅限于间接层面,而不直接及于行政相对人。因此,就整体而言,裁量基准发挥行政自制功能是以外部行政法为前提的,这在总体上保证了行政自制理念的提倡不会滑向德治,同时其也更加能够凸显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的补缺功效,这正是上述所谓的合法性基础,也是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在裁量基准制度中的完美结合。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归于行政自制规范范畴的裁量基准尽管并不直接引入诸如立法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的横向监督,但并不因此而丧失民主正当性。传统观点认为,行政机关的代表性或民意基础相较议会而言更为薄弱,并且不具有多元组合的特征,其所体现的反倒是政治的片面性或单一性;同时,在程序上,行政机关的议事程序亦相对较为简便、弹性及灵活,相较议会或司法而言,其欠缺谨慎与彻底性。因此,其是否认行政主体的法律行为含有正义内容的,在宪政体制的“正当性链条”中,类似裁量基准的行政规则通常也并不被理解为能够获得民主正当性,或者说其正当性微乎其微,甚至于传统理论更加倾向于“行政命令订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封闭的暗箱操作,其对外公开的只是讨论的成品,而非讨论的过程”(注: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第180页。)。正因如此,尽管传统理论中亦有类似行政自制的“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理论”(注: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但其依旧是将落脚点置于司法权之上,依靠宪法上的平等原则而最终达成行政自我拘束的控权效果。传统理论由于虑及欠缺民主正当性的行政机关并不负有政治上的义务而践行自我规制,对“纯粹的行政自我拘束”并不予以信任,因而往往会在其体系之外添加司法权的制衡。
但是,伴随国家与宪法结构的变迁,上述否定政府能够直接获得民主正当性的观点现在看来却是有待商榷的。批评者认为,只要人们进一步观察,就不难发现,行政权所订定的行政命令其实也具备一般性、公开性与预见性的特征。基于行政正当程序要求的日渐推行,行政机关亦开始注重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在注重程序正义的英美法系,类似议会立法的行政规则的作出,往往需要经过严谨的协商过程和繁杂的行政程序。譬如,在美国,正式行政行为的作出需要在程序上经历类似立法程序的通告与评论程序,而即使是非正式行政行为的作出,“也包括从完全没有任何程序的口头谈话,到几乎接近审判型的听证程序在内”(注:王名扬:《美国行政法》,第532页。)。在这一过程中,相对人的利益表达畅通无阻,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通过诸如听证的程序方式得到表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其和公民向国会输送正当性的选举方式一样正式和非同凡响,而行政机关也正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角色,政府与国会其实享有相同的、直接的民主正当性。这意味着,行政自制的义务来源并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行政自我拘束尽管拒绝司法权的保障,但其本身并未因此而丧失民主精神。在现代社会提倡的正当程序中,政府获得了不同于国家公权力的社会力量的督促,这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行政自制不会流向空洞。因此,行政自制在政治层面亦是具有有效性的,裁量基准的控权逻辑也因而是有效的。
2 .异于传统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裁量基准控权逻辑的有效性获得,除上述行政自制的合理性证明路径之外,实际上与其异于传统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存有密切关联。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规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我调控”式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所谓功能主义建构模式,作为相对于传统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而言的一种重要的裁量治理模式,主要是一种“政府自治”的风格,强调的是行政的自我治理,通过行政裁量运行系统内部各种功能要素的自我合理建构,来充分展现其固有的能动性和实现个案正义的内在品质。(注: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为视角》,《法学家》2011年第4期。)我们认为,裁量基准控权逻辑的有效性获得,在根源上是由此而决定的。
首先,按照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的理解,在形式上,裁量基准尽管也以“规则”的形式出现,和传统的规则主义控权进路相差无几,但有所不同的是,裁量基准强调的是对裁量权的一种主动、内发的“自我约束”,而不是机械式的“自我压制”,更不是一种来自外部力量的“被迫”。裁量基准强调的这种“自我约束”主要通过一种“自我调控”式的建构功能来实现,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自我建构。尽管裁量基准也具有限定和制约的功能,但这种“限定”主要是为了将裁量权控制在合适的限度内,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对裁量的调节建构功能,“制约”更是“建构”的延伸和保障。在目的上,它是为了达到裁量权的正当行使,而非对裁量空间的“压制”甚至“取消”。因此,在控权逻辑的有效性问题上,裁量基准便在制度源头上获得了较之传统而言更为优越的主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控权逻辑能够顺利展开。
其次,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尽管讲求自我要求,但在规范立场上,功能主义却因为饱含有限性和开放性两项特征,而不会滑向“行政专断”的尴尬境地。具体表现为:其一,功能主义建构模式中所能展现的控权效果实际上是有限的,它在本质上往往也以“原则之治”为根本追求,是一种“以法律原则为取向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注: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第41页。)。它既反对绝对意义的“规则至上”,也不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政府自治”,而是在法律原则主导下的行政自我治理。一般而言,具有功能主义表征的裁量基准,并非不受法的约束,只不过这种“法的约束”主要来自法律原则。我们除了需要继续秉承传统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将裁量基准严格限制于行政法定原则之内,以确保裁量基准不逾越法定的权限范围之外,还必须在制度上引入比例原则,完善行政参与和公开公布机制。以“法律原则”为限定的积极功能在于,其在规范行政行为的同时,亦不至于落入规则主义的主观俗套之中,而这正是功能主义的精髓所在。其二,按照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的理解,裁量基准的控权逻辑也并非封闭的,与现阶段的行政自制理论有所区别,功能主义立场下的、内含于行政自制理论中的裁量基准并不排斥他制,其本身是开放的,既会被置于“框架性立法”之下加以检讨,也会接受变化了的司法审查,从单纯“法律控制”的司法审查变向为“过程控制”。同时,从裁量基准既有的立法技术加以观察,裁量基准内在的制度设计同样也不会抵触“他制”要素的嵌入。现阶段不仅各种内设机制之间是相互联动、协调一致的,而且取源于执法经验的制定程序,实际上也融合了公众的智慧。因此,裁量基准控权结构的开放性,便可以避免控权技术使用的单一选择,能在最大限度上将自制与他制归为一体,从而贴近实质法治的现实需求。这些在整体上保证了裁量基准控权逻辑的有效性能够获得更为现实的澄清与说明。
(四)小结:对于正当性质疑的回应
“现代国民不仅必须守法,‘与法律共同生活’,也必须遵守数量庞大之行政命令,与‘命令共同生活’,行政命令对人民权利义务之影响不可谓不钜。”(注:许宗力:《论国会对行政命令之监督》,《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8年第2期。)在现代社会中,基于权力分立而架构的宪政体系已经不拘泥于古典的“法律保留原则”学说而战战兢兢,彼时具有“过高法治期望”的禁止授权原则也早已被束之高阁。恰恰相反的是,现代社会的行政命令往往能够通过理论自身的扩张解释以及实践自发的创新尝试而获得实证意义与认可。然而,由于我国宪政话语的冷清,裁量基准从一开始便只是被作为一种技术现象来对待,而并没有被置于宪政主题中检讨其正当性或合法性。抛开传统的规则主义路径,转而基于行政自制和功能主义的立场,我们就会清晰地认识到,在将裁量基准的属性定位为行政自制规范的逻辑起点下,形式上体现为规则主义的裁量基准的“权力来源”是具有合法性的,同时,功能上体现为行政自制的裁量基准的“控权逻辑”亦是具有有效性的。因此,总体而言,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是具有正当性基础的。据此,作为理论回应,我们完全可以对前述的相关质疑予以澄清。
1. 对于认为裁量基准权力来源具有合法性瑕疵的认识。按照前述论证,在规范主义角度,裁量基准权力来源是不存在违法性瑕疵的,无论是在域外,还是在我国宪政体制中,它都具有合法性基础。实际上该认识只是看到了裁量基准的形式特征,而没有注意到其实质的控权逻辑,其在属性定位上存有片面性。倘若虑及裁量基准亦具有行政自制的品质,我们自当会注意,实践中并不存在创设权力、权利及义务的基准文本,它只是对授权法的细化,其约束的是行政机关自身,而并非相对人。在授权法前提下,一个主体自我要求“从善”,我们完全没有质疑其合法性的必要。
2 .对于认为裁量基准控权逻辑不具有有效性的认识。裁量基准在授权法与民主正当性前提下,自当不会由于过分依靠德治而陷入行政专制的尴尬境地。在另外一端,和上述观点类似,那种认为裁量基准可能会导致裁量僵化的认识同样是对功能主义立场的忽略,其并没有观察到裁量基准行政自制的控权属性。很明显,在欠缺宪法与组织法的义务规定下,裁量基准的义务来源只是其自律精神的施舍。在意志前提下,一个主体自我要求“从善”,自当不会真的“作茧自缚”而致自己“苟延残喘”,如此,上述担忧便可能也仅仅是杞人忧天罢了。
3 .相应的,在已经确定裁量基准权力来源合法及控权逻辑有效的前提下,司法审查对于有着行政自我拘束品质的行政行为,便理所当然地需要给予最为基本的尊重。正如前文所述,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其本质属性的主要成分是行政自制,那么,在尊重与戒惧的权重过程中,司法态度便应该更加偏向尊重一方。对此,可以作为补充说明的理由是,对向来秉承规范主义立场的司法审查而言,裁量基准并不会出现较大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实践中的基准文本大多会保持对“授权法”的基本尊重,而此种尊重当然也应对应地延续到司法审查的基本态度之中。
三、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度边界
我们已经看到,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规范,无论从其权力来源的合宪性还是从其控权逻辑的有效性而言,都已获得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问题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克服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治理模式所固有的局限性,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内在的自我控权功能,归根究底还得取决于一种正当化的制度安排。对此,我们必须为其划定一个合理的边界,以从制度层面上保障裁量基准正当性的实现。
(一)制度上的局限性之克服
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自制型的行政规范,在制度上同时存在着来自其固有的作为“规则之治”与作为“行政自制”两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严格规则之下无裁量。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制,力图用普遍的规则来细化和统一裁量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规则中心主义”的进路,仍然存在着与后者类似的局限性,即过分依赖于严格的规则而导致裁量范围过窄,进而丧失其应有的能动性。这样的裁量范围有如戴着脚镣跳舞,又怎能实现个案正义呢?从根本上讲,裁量的存在主要服务于个案正当性,而一种“规则化”裁量基准的制定则是“一般裁量”或立法性裁量权的体现,由于“一般裁量与个别裁量可能发生冲突”(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128页。),因而过度规则化的裁量基准必然会损害个别裁量权的正当性。(注:对此,有学者专门提出了裁量基准过度规则化存在的弊端:(1)规则的膨胀致使行政人员无所适从;(2)大量的规则会使行政人员以规则为目的而忽视行政活动本来的目的;(3)大量的规则忽视了行政人员的能动性,从而将行政人员变成了规则的执行机器;(4)大量的规则会提高行政成本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参见崔卓兰、刘福元:《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规则化》,《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其次,“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注:[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第248页。)。过分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自制”或对行政机关立法性裁量权的大量授予,很可能会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而且会导致一种新的“行政专制”。
显然,裁量基准固有的这两个方面的局限性,正是人们对裁量基准存在的正当性产生质疑的重要缘由之所在。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克服裁量基准这种固有的局限性,才能保障其正当性的实现。对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层面为裁量基准划定一个合理的边界,以实现其沟通法律与个案的结构功能优势,真正发挥其在限定、建构和制约裁量权等方面的内在功能作用。具体而言,在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构建中必须充分把握三个方面的平衡,即在羁束与裁量之间的平衡、在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平衡以及在自制与他制之间的平衡。
(二)在羁束与裁量之间的平衡
裁量基准旨在通过规则羁束限制裁量,但是从行政执法实践来看,由于规则往往过于僵化而使得执法者蜕化为类似于自动售货机的执法机器,由此给裁量的个别正当性造成损害,这正是裁量基准作为“规则之治”的最大局限性之所在。因此,一个设定科学、运行合理的基准,应该能够满足在行政裁量的规范性与能动性、羁束与裁量之间平衡的技术要求。
首先,在效果的格化上,应当预留一定的裁量幅度。一般来说,裁量基准不宜采用直接指向一个单一固定的处理结果的“定额制”,它应把法律规定的裁量种类、幅度分割和格化为相互衔接的“段”而不是孤立的“点”,使得执法者在基准之下仍能能动地根据不同个案的具体情况而选择效果与情节相当的最优结果,不至于完全剥夺个案裁量的空间。例如,杭州市旅委制定的《〈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行政罚款裁量规则》(注:杭旅政法[2008]222号。)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格化为1000元、2000元和4000元这三个孤立单一的固定金额。这在实践中极易陷入粗糙和粗放的尴尬之境,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个案正义的要求。(注:还有一种“公式化”的裁量基准也是欠妥的。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行政罚款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就规定了一种罚款公式,即在风景区内饲养家禽家畜的,罚款数额=最低额(20元)+自由裁量度(1000元—20元)×(家禽数量/10只)×100%(10只以上按最高额处罚)。按照该公式,养1只鸡罚118元,多养一只鸡多罚98元,养10只鸡以上罚1000元。如此精细化的公式计算,实际上取消了个案裁量。笔者认为,即便采取这样的罚款公式,也应当在情节的细化方面留有余地,并采取科学的统计指标分析方法。详见下文第三章“行政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同时,在划分具有幅度空间的处罚格次的基础上,格次之间应有升降的机制,格次之内亦应有增减的机制。例如,金华市公安局制定的《赌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试行)》规定,具备特定的严重情节的,应提高一个档次处罚;而具备特定的酌情从轻情节的,则可考虑在同一裁量格次内降30%以下幅度裁量,此即格次之间的升降机制和格次之内的增减机制。这两个技术细节令基准对处罚的格化不再机械和呆板,而使各个处罚格次成为一个衔接有致、转换畅通和有机联系的整体,所以亦为裁量基准所应必备。
其次,在情节的细化上,应当预含有限的情节判断余地。情节判断余地,是指裁量者在情节的提取认定、判断比较和考量适用等方面所拥有的自主决定空间。赋予执法人员相应的情节判断余地,对于鼓励能动执法以追求个案正义、避免基准陷入僵化之虞来说,同样是极有必要的。一方面,执法人员对基准所列明的情节,根据其在具体个案中的重要程度,享有“具体个案具体决定”的判断余地,因为每项情节在特定个案考量中的相关度和重要性都是因案而异的,建立一个固化的统一判断标准其实是不利于个案裁量的。另一方面,执法人员对于基准所没有具体列举但又在个案中出现的情节,具有增加和补充的权力。基准对于裁量情节的细化规定,也会面临空间上的不周延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而情节细化的开放性设置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这种“成文病”。对此,在细化列举裁量情节时,应设定情节的兜底条款。例如,金华市公安局《赌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14条第6项即设置了“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这样的兜底性规定,这样,对执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第14条之外的其他严重情形,如为未成年人赌博提供条件的,执法人员就拥有纳入情节考量范围的增补权,保证了最终的处罚结果更好地符合个案正义的要求。
当然,这种情节的判断余地应该是有限的。对情节判断余地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禁止情节考虑的恣意。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所云:“如果一个法律上之区别对待或相同对待不能有一个合乎理性、得自事物本质或其他事理上可使人明白之理由,简单地说,如果该规定被认为是恣意时,则违反平等原则。”(注:张锟盛:《论析禁止恣意原则》,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三民书局1994年版。)情节考虑的恣意是对基准所追求的平等对待的悖反。对于执法者来说,应当禁止“不相关考虑”,考虑应当考虑的情节,而不考虑不应当考虑的情节,纳入考量范围的裁量情节应与个案事实之间具有合理的、充分的、实质上的联系和理由。二是情节的设置也不能过于宽泛。作为对法律规范的细化,基准本身应当尽量避免不特定法律概念和模糊语言的运用,而应设置明确具体而又丰富多元的情节。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某些裁量基准只把情节粗糙地细化为“情节较轻”、“情节一般”和“情节较重”,或者“初次处罚”、“二次处罚”和“三次及以上处罚”(注:例如,《苏州市交通局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情节较轻或危害性较小处罚3万元;情节较重或危害性较大处罚5万元;情节严重或危害性很大处罚10万元。”“不符合从事客货运经营规定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初次处罚500元;两次处罚1000元;三次及以上处罚2000元。”)。实际上,这样的基准在实践中能否有效规制裁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裁量基准制度的运用最直接的目标仍是在于控权,防止基准过于抽象,使其技术更为精细,(相对于防止基准的僵化)在任务上更为迫切。”(注:朱新力、骆梅英:《论裁量基准的制约因素及建构路径》,《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
再次,在基准的适用上,应当预设逸脱程序和例外条款。基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指挥监督权,裁量基准具有一种对内的拘束力,下级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对裁量基准应当严格遵照执行。但是,立法者授予裁量权旨在追求个案的正义,行政机关在行使个别裁量权中对于裁量基准并未予以揭示的考虑事项,仍然负有个别情况考虑的义务,而不能机械、僵硬地适用裁量基准作成具体决定。对此,裁量基准应通过“授权规定”预设逸脱程序,允许行使裁量权的机关根据个案逸脱裁量基准的边界,以实现个案正义。但也要对逸脱程序加以严格限制,如采用说明理由制度、集体会办制度和逐级报批制度等。也就是说,执法人员应当能够说明正当和充分的逸脱理由,并且严格遵守集体会办或逐级报批的程序要求,否则禁止逸脱基准的边界。此外,基准还应当设定例外条款,即明确法律法规、行政政策或者情势变更对于基准的优先适用效力。例如,《金华市公安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实施意见》规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与法律法规冲突的,应以法律法规为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实施后,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的,或当地社会治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进行修改。”
(三)在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平衡
在对待裁量基准的边界上,不仅要避免裁量基准的过度“规则化”,还要防止裁量基准成为一种新的“行政专断”。对此,法律原则以其所特有的抽象化特征而发挥着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或者填补规则之漏洞的作用,并发挥着较之于行政规则更强的规范化预期作用。(注: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8页。)无疑,法律原则在保证行政的必要灵活性、同时又有效制约行政专断这两个方面,都是有益的。(注:See Phillip J Cooper, Publi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2nd edition,1988,p 103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裁量基准作为立法对裁量权进行“法的约束”的一种延伸,这种“法的约束”主要来自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设定裁量基准的法律依据。因此,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制,并非一种绝对的 “规则至上”,也非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政府自治”,而仍然应当以法律原则为取向,定位为一种在法律原则主导下的行政自我控制机制。对此,一方面必须将裁量基准限制于法律优先、法律保留等行政法定原则之内,以协调这种行政自我管制与依法行政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并防止出现新的“行政专断”。另一方面,裁量基准作为对裁量权行使的一种程序性实体约束,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与个案裁量中的利益衡量并无实质的区别,因此必须遵循作为利益衡量一般原则的比例、平等对待、信赖保护等行政均衡原则(注: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第200页以下。),以保障其实体内容上的客观、公平、公正,使裁量的实体内容获得最佳建构。
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关系,使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与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相适应、成比例。平等对待要求行政机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或按比例对待”,具体包括禁止恣意、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子原则。其中,禁止恣意原则不仅禁止行政机关的故意恣意行为,而且禁止任何客观上违反宪法基本精神以及事物本质的行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裁量决定时,若无正当理由,应当受先例或惯例的约束,对于相同或同一性质的事件作出相同的处理。根据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后,不允许政府随意变更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无论是比例原则,还是平等对待和信赖保护原则都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裁量基准时,应当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因素,充分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以设定最佳的判断选择标准。
就行政处罚领域来说,《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了行政处罚应考虑的基本因素是“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据此,裁量基准的制定应当根据这些基本因素,并充分考虑各因素的主次情况、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量罚幅度,具体细化为若干裁量格次,并规定每个格次所给予的不同量罚标准,以求解量罚最佳适度点,确保“过罚相当”,防止轻错重罚、重错轻罚。在实践中,凡是按照固定比例,或以一律按照法定最高限额或最低限额进行处罚等情况而设定的裁量基准,事实上都是有违比例原则的。违反比例原则而制定的裁量基准,将丧失其存在的正当性。在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审查实务中,已有成案对不合比例原则的裁量基准作出了否定性的判决。如法院在违规营业罚锾案(93 判字第1127号)判决中认为:
行政机关基于行使裁量权之需要得根据其行政目的之考量而订定裁量基准,此种裁量基准可由行政机关本于职权自行决定无须立法者另行授权,然仍应遵循立法者授权裁量之意旨。故行政机关于订定裁量基准时,除作原则性,或一般性裁量基准之决定外,仍应作例外情形时裁量基准之决定,始符合立法者授权裁量之意旨,以为具体个案之正义。被上诉人八十九年(2000年)六月三十日订定之《电子游戏场业违规营业罚锾金额标准》,关于违反电子游戏场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第六款者,一律处以250万元最高额罚锾,嗣于九十年(2001年)四月三日修正,亦仅分为第一次处罚锾240万元,与第二次以上(含第二次)处罚锾250万元而已,虽较修正前略有改进,但与电子游戏场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罚锾部分之法定范围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相去甚钜。且由附于原处分卷之该电子游戏场业违规营业罚锾金额标准观之,其仅作原则性,或一般性裁量基准之决定,并无作例外情形时裁量基准之决定,自未能达成具体个案之正义,无异于将法定罚锾数额下限提高为240万元,诚难认其符合立法者授权裁量之意旨。此部分之电子游戏场业违规营业罚锾金额标准,于法自有未合。被上诉人依上述标准,裁处上诉人罚锾240万元,其裁量显与法有违,诉愿决定及原判决递于维持,尚有未洽,上诉意旨执此指摘,并无理由,应由本院将原判决该部分废弃,并撤销该诉愿决定及原处分,由被上诉人依立法意旨,确实裁量,另为处分,以期适法。(注: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93)判字第1127号判决,见http:
//fyjud.lawbank.com.tw/list.aspx。)可见,行政机关基于行使裁量权的需要,有权根据其行政目的的考量而订定裁量基准,但仍应遵循立法者授权裁量的旨意和目的。这里的立法授权旨意和目的,主要体现在“法律原则”之中,包括比例原则、平等对待、信赖保护等原则。在上案中,被上诉人所定《电子游戏场业违规营业罚锾金额标准》,将法定罚锾数额下限提高为240万元,法院认定其不符合立法者授权裁量之意旨,有违比例原则,从而作出了否定性的判决。
此外,平等对待和信赖保护原则还直接影响到裁量基准的适用效力,要求行政机关对已经设定和公布的裁量基准必须适用并不得随意变更,如需逸脱或变更,都必须有正当理由,否则构成违法。(注:参见本章“四、裁量基准的效力界定”。)
(四)在自制与他制之间的平衡
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的形式,在性质上主要是对裁量权的一种自律性约束,因此在没有“他制”的情况下,其有效性的发挥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尽管行政机关在这个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毕竟也是有局限的,完全依赖于这种技术专家式的自制,极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行政专断”。因此,这种自律机制的设计必须依赖于他律因素的嵌入。对此,既需要适当引入行政系统外部的“他制”,也需进一步完备行政系统内部的“他制”。这些制度通常被设计为公众参与制度、公开制度以及行政系统内部的评议考核、责任追究、责令说明理由制度和报备审批程序等制度。当然,这里需要对这些制度作进一步的检讨。
首先,关于公众参与制度。鉴于实践中裁量基准的制定完全依托行政机关自身力量,纯粹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内部自我生成机制,笔者曾经建议:“为了保证裁量基准的民主性和规范化,行政主体应当尽可能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参与裁量基准订立的各种条件和机会,透过立法引导与行政推进并举,保障民众广泛和直接参与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注: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对此,有学者提出:“裁量基准是在立法授予的裁量空间中的再创造,而立法的民主性已然解决,在十分有限的授权空间中,民主元素添加与否,意义并不彰显,这种再创造将更多地依靠行政机关的经验、技术和智慧。”(注: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但是,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尽管裁量基准制定的程序有别于立法程序,因为前者应当“既经济又有效率”(注: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1,p 65 ),所以不必过分加入立法程序的民主元素而完全采取类似如正式听证这样的公众参与形式;但是为了增强裁量基准的科学性和相对人的可接受性,必须适当引入具有他制元素的相对或有限的公众参与机制,如广泛征求、听取一线行政执法人员和相对人的意见。(注:如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通知》(琼府办[2009]3号)规定:“在(基准的)细化过程中,应当广泛征求市、县相应行政执法部门的意见,同时要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 “要在广泛征求、听取一线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管理相对人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划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阶次,列举与行政处罚阶次相对应的情形,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基准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一线执法人员的经验十分重要,基准实际上是执法经验的总结,其设定是否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经验是否成熟。此外,让专家参与裁量基准的起草和论证,也有助于裁量基准的理性化和正当化。
其次,关于裁量基准的公开制度。裁量基准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规则,严格说对外并不具有拘束力,但由于它构成了裁量权的判断标准,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也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而目前理论上普遍坚持裁量基准“必须公开”的观念。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制度的设计,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1条第2款规定:“裁量权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开。” 《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第8条也做了同样的规定:“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应当坚持公开原则,自由裁量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然而,在对待裁量基准的公开性问题上,我国目前的实践以及域外的态度都是相当谨慎的。例如,较早在我国推行裁量基准的金华公安局在实践之初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公开,而是采取“逐渐公开”的策略。(注:参见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笔者于2009年7月23日—25日赴金华市进行的专门实证调研也基本印证了这一事实。)更有意思的是,《金华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意见》只要求各行政执法机关将本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在办公场所”进行“公示”。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2节规定,必须在联邦登记簿上公布“机关制定和采取的基本政策的说明和机关采取的普遍使用的解释的说明”。然而事实上“法院是很少强迫行政机关执行上述条款的”(注:Russell L.Weaver."An APA Provision on Non-legislative Rules",in 56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4),p.1187 )。同样,在日本,《行政程序法》对审查基准采取的表述是“必须”公开,而对“处分基准”却是“尽量”或“努力公开”(注:[日] 横川隆生:《审查基准、程序性义务与成文法化——有关裁量自我拘束的一则参考资料》,朱芒译,《公法研究》2005年第1期。)。另外,需要注意,日本《行政程序法》在裁量基准公开性问题上,亦区分了“公布”与“公开”的不同含义,立法者采用的是“公开”而非“公布”。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开’并不要求行政厅承担如‘公布’那样广而告知的义务”(注: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从裁量基准的实践及域外在对待公开性问题上的这种“谨慎”态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对裁量基准“必须公开”的观念予以重新检讨。笔者认为,或许建构一种“相对公开”理念,更加能够与裁量基准控权原理相融合。从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自律技术来看,行政机关并不负有“必须公开”的义务,因此裁量基准的公开可以树立类似日本《行政程序法》对“处分基准”采取的基本态度——“努力公开”的立法表述。而即使是努力公开,在具体公开方式上,我们也并不苛以广而告之的任务,并不必须要求行政机关像行政立法程序那般严肃和僵化。实际上,“行政机关公开法律与政策的方式不一而足,有非正式的也有非常正式的。例如,工作人员的非正式谈话、行政机关成员的私下说明、行政机关代表的公开讲话、行政机关的新闻发布会、官方的政策说明等类似的形式。……所有这些沟通方式都是非常有益的,应当加以利用”(注: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p 102 )。无疑,“相对公开”的理论预设,能够较好地满足“自制”与“他制”之间的平衡要求。此外,按照“相对公开”的理念,裁量基准的公开可以根据其成熟度来决定,对于已经成熟的裁量基准应当尽量公开,提前使之普遍化,而对于那些认为还不成熟的裁量基准,也可以在个案裁量中以说明理由的形式向特定相对人予以公开。这样,通过具体个案经验到典型个案经验的积累再到基准的普遍化,基准的科学性也会大大增强。
此外,尽管前述裁量基准设定中“职能分离”机制已成为一种内在的“他律”因素,但这还远远不够。在行政系统内部,为了确保裁量基准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必须建立相关的评议考核、责任追究、责令说明理由制度和报备审批程序等制度。这些制度的联动,相对于裁量基准制度而言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他律”因素。如,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淄博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方案》(注: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10月31日发布。)第5项专门规定了“建立评议考核制度”;《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注:江苏省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2006年5月12日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第12条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应当依据《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和《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试行)》(注:深工商法字[2005]16号。)第12条规定,对当事人依法从轻、减轻、从重或者免予行政处罚,相应法定情节必须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第14、15条规定,逸脱裁量基准的案件在审批程序上要经过:办案机构→核审机构→分管局长→局长办公会议的审查批复。这些都说明裁量基准的约束力是刚性的,公务员没有适当的理由和有效的证据以及履行逐级报请批准的程序就无法逸脱裁量基准的边界。
四、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界定
严格规则之下无裁量。这是裁量基准作为“规则之治”的最大局限性之所在。为此必须通过诉诸前述制度层面的边界划定来保障其正当性的实现。然而,面对裁量基准这样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制规范,仍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其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具有法律拘束力,则很有可能因为严格拘束于“规则化”的基准而导致适用上的机械、僵化,犹如戴着脚镣跳舞,又怎能实现个案正义?若没有强制约束力,那它是否又有存在的必要?这无疑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对此,需要在区分对内与对外效力的基础上,对裁量基准的效力范围加以合理的界定。否则,仍然很难克服其制度上固有的“规则化”之局限性。
(一)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效力
如前所述,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内部制定的一种行政规则,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是一种合宪性机制。既然如此,裁量基准当然就具有一种对内的拘束力,下级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对裁量基准应当严格遵照执行。
裁量基准对内效力的根据主要源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指挥监督权,即根据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行政机关基于行政隶属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具有指挥监督权。同时,从行政体制上公务员的服从义务来看,我国《公务员法》第12条第5项规定,“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第53条第4项规定,公务员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制定的一种内部性行政规则,本质上属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发布的一种职权命令,因而对下级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具有当然的拘束力。对此,在我国裁量基准“规则化”推进的实践中,几乎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许多涉及裁量基准的规定中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执行和遵守都有明确的要求。譬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1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遵守裁量权基准”。这意味着裁量权基准对制定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都具有拘束力,它们都应当遵守。(注:参见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编:《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有些涉及裁量基准的规定则在程序上明确要求“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具有与“规范性文件”同样的内部拘束力。如《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第9条规定:“市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后公布实施。”《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59条规定:“行政执法不得滥用行政裁量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行政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从域外来看,日本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裁量基准这类行政规则在行政组织内部具有拘束力(注: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69页;[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第72页;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德国学者则认为,裁量基准这类行政规则本来就是一种内部规则,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约束力是其作为法律上规则的法律特征;根据公务员法上的服从义务,有关机构成员应当遵守和适用行政规则。(注: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592、597页。)
裁量基准对内的拘束力主要是基于行政机关的领导权或监督权而产生,但往往还需要借助于行政机关内部激励、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等自我约束机制来得以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行政机关体系中,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通过内部的执法质量考评、执法监督检查、行政复议和信访等机制,通过系统内外的监督合作,足以使裁量基准‘令行禁止’,具有甚至比法律还强的、还有效的拘束力和执行力。”(注: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透过目前裁量基准制度推行的实践来看,多数行政机关都建立了相应的内部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裁量基准对内的拘束力。如,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淄博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方案》(注: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10月31日发布。)第5项专门规定了“建立评议考核制度”。它规定:“按照市政府的依法行政考核办法,结合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由市实施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行政执法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分别制定市政府和各部门(系统)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及依法行政评议考核。不执行已经规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要记入档案并记分;对主管领导和分管领导,由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依法行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试行)》(注: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06年1月25日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第9条规定:“各行政执法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内容进行年度考核、考评。对因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当影响案件办理质量的,按照《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追究有关行政执法机构及行政执法人员的过错责任。”《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注:江苏省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2006年5月12日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第12条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应当依据《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和《南京市文化局(市文物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当然,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裁量标准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其所执行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对该行政执法机关有拘束力的是该行政法律规范本身;上级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标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行政内部规定。——这意味着违反上级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标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注: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笔者认为,尽管裁量基准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其所执行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因此该法律规范对行政执法机关具有拘束力,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排除该裁量基准也具有拘束力。事实上,行政执法机关在适用裁量基准时,面临着法律规范与裁量基准的双重约束。而在法律位阶中,法律规范的效力明显会高于裁量基准,法律规范具有优先于裁量基准的地位。但是,“优先意味着发生冲突时上位阶的法律规范有效,应当予以适用,而与上位阶法律规范冲突的下位阶规范无效,不予以适用”(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70页。)。据此,在裁量基准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法律规范的效力为准,优先适用法律规范。但是,效力的优先性并不同于适用的优先性。“位阶确立的是上阶位规范效力的优先性,而不是其适用的优先性。实践中往往是优先适用下阶位的规范”。“适用的优先性来自在各个规范更为具体、更可实施的法律的约束力”(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73页。)。因此,尽管法律规范在位阶上的效力具有优先性,但具有更强可操作性、更具体的裁量基准在适用上则具有优先性。在实践中,应该首先适用裁量基准,只有在裁量基准与法律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下才认为裁量基准违法,或者应该被撤销或者不予以适用。
(二)对内效力的例外:个别情况考虑义务
裁量基准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拘束力,意味着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裁量基准,完全一律地适用裁量基准作出行政决定,而不得与之相违背,否则即构成违法。但有学者认为:“违反上级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标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注: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对于特殊情形,应该允许执法机关作出不同于裁量标准的规定而作出处理决定。”(注:王贵松:《行政裁量标准:在裁量与拘束之间》,《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在国外,亦如此认为:“行政法认可使用指导方针、指令和手册等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建构着裁量运作,但同时也要求决定的作出者应当根据个案的需要,去逸脱这些指导方针,以避免裁量受到束缚。”(注:Geneviève Cartier,"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the Spirit of Legality:From Theory to Practice",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9,24 No.3,p.325 )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作为裁量基准效力例外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或逸脱裁量基准的问题。
根据行政裁量的立法授权旨意,立法者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目的旨在追求个案正义,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决定时必须综合考量个案具体情况。“当下级行政机关完全一律地适用裁量基准作成行政决定时,是否与立法者授予裁量权追求个案正义的本旨相违背,不无疑义。”(注:王志强:《论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东吴大学法学院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4页。)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70条第3项的规定,客运经营者在运输途中擅自将旅客移交由他人运输,处罚标准为1 000—3000元。《苏州市交通局交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初次违规处罚1000元,第二次处罚2000元,第三次或者以上处罚3000元。显然,该裁量基准仅以违规次数作为处罚的唯一依据。然而,倘若行政机关在个案中仅仅是考虑有没有前科,而不再考量其他相关事项,如行为人违规情节轻重、造成损害大小、主观过错、悔改表现等因素,难以想象如此可以实现个案公正。因此,行政机关在行使个别裁量权中对于裁量基准并未予以揭示的考虑事项,仍然负有个别情况考虑的义务,而不能机械、僵硬地适用裁量基准作成具体决定。也就是说,上级机关已经制定的裁量基准并不能当然地剥夺下级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下级行政机关因考虑个案的特殊情况而逸脱该裁量基准的羁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违法。
但是,这里的“个案的特殊情况”必须是构成逸脱裁量基准的正当理由,并遵循正当的说明理由程序。“不说明理由或理由不成立的行政处理是越权行为”(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183页。)。从确保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平等对待以及信赖保护等原则的要求来看,行政机关要作出与裁量基准不同的判断,也必须具有合理的理由。如果不能作出充分的说明理由,就有滥用职权之嫌疑,甚至产生违法的问题。(注: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第76页。)实际上,根据现代法治的要求,任何裁量权的行使都必须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否则就会导致裁量权的滥用或不当。这种裁量判断标准即裁量权行使的正当化理由。裁量基准作为对裁量权行使判断标准的补充,只不过提前以规则的形式公开了这种判断标准,其实质就是裁量权行使或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或理由。当裁量基准符合授权法的授权目的和立法意旨时,行政机关依据该裁量基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即属具有正当的理由。因此,尽管根据立法授权旨意,行政机关基于个案特殊情况的考虑,可以逸脱裁量基准而作出不同于该裁量基准的行政决定,但该“个案特殊情况”必须构成不同于该裁量基准的其他正当理由,并且作出决定者负有说明义务。而该“个案特殊情况”是否正当,亦有赖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裁量决定之前,事先探求授权法的授权目的和立法意旨。只有行政机关履行了个别情况考虑的义务且该个别情况系属于符合立法旨意的正当化理由,其不按照裁量基准作出具体行政决定才属合法。在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在对待裁量基准适用过程的审查态度上,亦往往如此。对此,可以透过周文明诉文山县交警大队案一例来观察。该案案情如下:
2007年8月2日,周文明驾车行驶至云南省文山县境内省道210线某处时,被文山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拦下,告知其行驶速度为每小时90公里,已超出该路段每小时70公里的限速,并以该超速行驶不满50%处以其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而根据云南省公安厅制定的《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处罚标准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三十一款的规定,“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未到50%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周文明据此认为交警罚款200元的处罚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交警罚款显失公正,变更罚款为80元。文山县交警大队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并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对超速行驶不满50%的上限处罚为200元罚款,而近年来,文山县所发的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超速行驶,鉴于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文山县交警一直对超速行驶实施该上限处罚。二审法院认为,云南省公安厅制定的该暂行规定仅属其内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法律、法规,原审法院适用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变更上诉人适用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罚内容于法无据,据此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文山县交警大队2007年8月2日对周文明超速行驶作出的公安交通违章简易行政处罚决定书;驳回被上诉人周文明的诉讼请求。(注:参见陈娟:《驾驶机动车超速,究竟罚多少:云南省公安厅红头文件引争议》,《人民日报》2008年4月2日,第15版。)
本案中,一、二审判决的结果截然不同,显然其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处罚标准暂行规定》这一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裁量基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应当受此约束,并适用该裁量基准作为审判的依据。二审法院则认为该裁量基准仅属行政机关内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2条(2014年修订后为第63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依据(注:《行政诉讼法》第52条(2014年修订后为第6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因而据此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在这里,二审法院同时还维持了文山县交警大队逸脱该裁量基准而作出的具体决定,其判决背后所隐藏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本案中,文山县交警大队之所以没有适用《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处罚标准暂行规定》这一裁量基准关于50—100元罚款的规定,而直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上限处罚作出决定,主要考虑了这样一个个案的特殊情况,即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且导致文山县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超速行驶。显然,二审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该个案特殊情况符合立法授予裁量权的旨意,属于正当理由,故而维持文山县交警大队逸脱该裁量基准而作出的处罚决定。从本案二审法院的态度来看,下级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裁量决定时基于立法授权的旨意仍然负有个别情况考虑的义务而无须僵化地适用裁量基准。也就是说,尽管裁量基准对行政机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基于个别情况考虑,则行政机关仍然可以逸脱裁量基准而直接依据法律规范作出决定。只不过该“个别情况”必须是构成逸脱裁量基准的正当理由,否则行政机关仍然应当严格遵守裁量基准,而不得与之相违背。可以说,让行政机关负有个别情况考虑的义务,能够较好地划定裁量基准的效力边界。
(三)对行政相对人的外部效力
我们已经看到,裁量基准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而获得一种对内的拘束力,除非基于个别情况考虑不得逸脱裁量基准的拘束。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裁量基准能否获得一种对相对人的外部法律效力。对此,有学者认为:“由上级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标准也只是一种行政内部规定,并不是具有拘束力的规则。”(注:王天华:《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周文明诉文山交警不按‘红头文件’行政处罚案”评析》,见
http://chenyuefeng.fyfz.cn/blog/chenyuefeng/index.aspx?blogid=429327,2010年1月17日访问。)域外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亦认为,裁量基准只是一种行政内部规则,其制定权在行政组织法上源于上级行政机关具有的指挥、监督权,其内容属于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并无直接关系的内部行政事务,也不构成法院裁判的标准,因此它只具有内部效力,而与法院及国民无法之关联。(注: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593页;[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第73页;[日] 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第69页;陈敏:《租税法之解释函令》,《政大法律评论》1997年第57期;陈春生:《行政规则外部效力问题》,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66—367页。)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类行政规则的功能日益扩大,外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从而使其直接或间接地具有了外部法律效力。因此,“现在普遍承认行政规则事实上的外部效果具有法律意义”(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599页。)。事实上,尽管裁量基准不属于一种立法性行政规则,并没有独立地创设相对人的新的权利义务,不具有独立的新的法律效果,但是它“在构建裁量结构的过程中,难免要涉及相对人的行为,或作为裁量考量因素,或作为识别标准,或者希望通过指导相对人活动而形成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无论哪种意图其效果必定会外溢到相对人,对规范相对人的活动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注:余凌云:《现代行政法上的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因此,从其实践效力来看,裁量基准一旦制定颁布,便不仅成为行政机关执法的重要依据,具有内部适用效力;而且当执法人员将该裁量基准所规定的内容适用于相对人身上时,这种内部适用效力将进一步延伸至行政相对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具有了外部效力。
不过,有学者仍然认为:“从实质性标准出发,行政规定如果不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即不属于法规命令,那么从理论上而言,当行政规定对行政职权体系之外的私人发生作用时(如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依据),该行政规定起着执行或解释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法律规范的作用。因此,当其内容涉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时,这些行政规定的内容的规范性应该归结于其上位的法律规范,即行政规定自身不应该具有外部的效果。”(注: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也就是说,即使裁量基准的内容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也应当归结于其上位法律规范本身产生的法律效果,裁量基准本身只是规范行政机关如何去适用该法律效果,并不具有独立的对外效果。但是笔者认为,既然裁量基准是对上位法律规范的具体化,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事实上是按照裁量基准对法律规范具体化之后的规定予以实现的,那么相对人就必须遵守该裁量基准的规定,否则就会发生裁量基准所规定的后果。因此,尽管裁量基准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作用,只是对上位法律规范适用效力的一种当然的影射,但也正是这种影射使得裁量基准对相对人至少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反射效力,即间接的法律效力。
从法理上言,裁量基准对外效力的正当化依据,源于其在个案中反复适用时所确立的行政惯例和所体现的法律原则的效力。也就是说,尽管裁量基准不具有直接的外部法律效力,但是可以通过其所确立的行政惯例和体现出的法律原则的适用效力而获得一种间接的法律效力。在德国,通行观点认为:“行政规则外部效果的根据是行政惯例和平等原则。行政规则通过稳定的适用确立了同等对待的行政惯例,据此约束行政机关自身。除非具有客观理由,不得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所谓的行政自我约束)。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无正当理由偏离稳定的、为行政规则确立的行政惯例,构成违反平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虽然不能诉称这种行为违反了只具有内部效果的行政规则,但可以诉称行政机关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平等原则,因为行政机关在本案中没有遵守已经实行的行政规则。如果行政规则调整的是给付的发放(助学金、补贴等),申请人还可以提出相应的分配请求权和给付请求权。”(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600页。)裁量基准就是这样一类行政规则,它是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裁量空间内,根据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行政执法的经验总结,按照裁量涉及的各种不同事实情节,将法律规范预先规定的裁量范围加以细化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如果行政机关据此对类似的个案反复适用,就形成了一种公平裁量的行政惯例或者行政先例,因此,按照平等原则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要求(注: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第218页。),行政机关在以后遇到同样情况时,也要适用该裁量基准作出同样情况的处理,即对今后行政机关遇到相同情形的个案处理具有拘束力。如果行政机关逸脱该裁量基准对相同情形的个案作出不同处理,则可以根据平等原则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认定该处理违法。同时,裁量基准的对外公布实施及其实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惯例对相对人还可能产生一种信赖利益,体现为“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在类似的个案处理中必须受到该原则的拘束,而不得逸脱该裁量基准,除非具有正当的理由。可见,“从裁量权公正行使之确保、平等处理原则及相对人之信赖保护等要求观点,与裁量基准为不同之判断,必须具有合理之理由,如果无法说明,则产生违法之问题。故裁量基准分类上虽非属法规命令,但在一定程度内,应认为具有外部效力”(注: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一)——行政行为形式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10页。)。
当然,在承认行政惯例和法律原则具有司法适用效力并作为裁量基准的效力依据的前提下,作为行政规则的裁量基准本身也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仅仅是行政惯例和法律原则的载体,因此并不直接构成对法院审判具有强制性和拘束力的依据。(注:参见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第100页。)当裁量基准违法时,法院仅能在其所审理的个案中将依据违法的裁量基准所作出的行政决定撤销,而不能直接宣告该裁量基准无效。但是与法律规范不同,法院有权而且应当审查该裁量基准的合法性,而不是无条件地援引和适用。通过审查,如果认为该裁量基准是合法有效的,就以此作为衡量和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和尺度,并在判决书中予以引用;如果认为它是不合法的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而不予适用,则事实上就否定了它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审查“裁量基准”的范围上,法院对其制定是否逾越法律之授权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有无滥用裁量权等情形都具有审查权,但一般不能及于其实质内容上的适当性审查。
在上海商业会计学校诉上海黄浦区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区劳动局根据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布的《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认定商业会计学校与陈老师之间存在特殊劳动关系,因此陈老师的伤属于工伤。商业会计学校则认为区劳动局认定其与陈老师存在特殊劳动关系所依据的该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合法性表示异议,在经过行政复议后向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依据该文件作出的工伤认定。黄浦区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其行政职权范围内,针对本市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作的规定。该规范性文件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审查,认为符合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基本精神,未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及在本案中的适用依法予以确认。”(注:《2007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法制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10版。)本案中,法院对作为行政规则的《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从该规则制定的权限、依据和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合法性审查,据此认定该行政规则合法,并将其作为衡量和判断区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这一行政决定合法性的标准而进行了适用。
可见,裁量基准对相对人的适用效力需要借助法院的司法审查才能最终得以确定,实际上是一种事实上的、可能的约束力,而并非类似法律那样具有当然的、必然的约束力。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如果法院支持裁量基准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则该裁量基准就具有了对相对人的约束力。而如果法院认为裁量基准不合法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而不予适用,那么该裁量基准就不会成为某项行政决定的依据,因此也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事实上就失去了其对相对人的效力。也就是说,裁量基准对相对人的适用效力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一般而言,裁量基准要获得对相对人实质的适用效力,需要具备如下条件:首先,裁量基准不得越出法律规范本身的范围,不能规定法律规范本身没有规范的事项,不能设立法律规范本身没有的权利与义务。其次,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执法权限,具有事务管辖权。再次,裁量基准应遵守法定程序,如经过一定的会议讨论、审议或经过一定机关批准备案等,只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符合程序正义,才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律效力。这种对相对人效力上的相对性,进一步划定了裁量基准的效力边界。
五、结语:功能主义行政自制观之提倡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深刻意识到,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规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我调控”式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从而有助于推进行政自制理论的发展及其内在机制的创新。
所谓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是相对于传统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而言的一种重要的裁量治理模式。在传统的规范主义看来,为使法治得到维护,任何一种权力都必须受到其他权力的严格制约和控制。行政裁量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权力,必须受到来自行政系统之外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控制。而且,这种权力控制都是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或“立法指令”为取向,是一种“法律控制”,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以“法律自治”为风格的“规则之治”。这种模式对于协调行政裁量与法治的关系,保证行政裁量严格受制于法治原则,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往往片面追求了形式法治,而忽视了实质法治;过分强调了严格的规则和机械的法律控制,而忽视了行政裁量固有的能动性与内在的自我调节功能,其结果只能是压制了行政裁量的生长空间和个性的自主发展。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自治”的风格。它强调的是一种行政的自我治理,即通过行政裁量运行系统内部各种功能要素的自我合理建构,来充分展现其固有的能动性和实现个案正义的内在品质。这种模式在充分发挥行政裁量的内在功能、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个案的正义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为了防止由于过分依赖行政机关的“自治”而可能导致一种新的“专制”,这种“自治”仍然必须被置于“框架性立法”之下,服从于一般性的立法规则或“法律原则”。因此在对待裁量的治理问题上,我们所倡导的应当是一种以法律原则为取向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注:参见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第41页。)
裁量基准是一种对裁量权的自我控制方式,这种自我控制虽然以“规则”的形式出现,体现的是一种“规则之治”的控权进路,但是有着不同于传统规范主义控权模式的明显特征:一是裁量基准强调的是对裁量权的一种主动的、内发的“自我约束”而非机械式的“自我压制”,更不是一种来自外部力量的“被迫”。二是裁量基准强调的这种“自我约束”主要通过一种“自我调控”式的“建构”功能来实现,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自我建构。尽管裁量基准也具有限定和制约的功能,但这种“限定”主要是为了将裁量权限定在合适的限度内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对裁量的调节建构功能,“制约”则更是“建构”的延伸和保障。因此都是为了达到裁量权的正当行使这一目的,而非对裁量空间的“压制”甚至“取消”。三是裁量基准强调的这种“自我约束”以“法律原则”为取向,从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法的拘束”,并非不受任何外部法律制约的纯粹“自制”或“自治”。四是裁量基准机制的运行不仅要求“内外互补”,还要求与行政系统内部其他制度之间形成相互联动、协调一致,以达到“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平衡。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特征,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规范,对裁量权的自我控制从本质上应当属于一种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无疑,这一认识对于拓展行政自制理论的视野(注:所谓行政自制,是指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该理论的提出,旨在为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而探求一条新型的行政自我控权路径。参见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以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行政自制的内在机制,都是十分有益的。
笔者以为,在我们极力倡导行政自制作为一种新型控权理论的同时,必须解决这样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行政自制作为一种对行政权的内部控制,与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外部控制相比,除了控权主体的“内外”有别之外,还必须充分把握这种控权的性质、功能与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否则必将难以有效,既无法取得与立法控制、司法控制相同的地位,于传统规范主义所强调的“行政控制”也难有所创新;二是行政自制的边界问题,过分强大的“自制”不仅可能导致一种新的行政专断,而且会让立法与司法的功能大打折扣,甚至缩减为零。对此,以功能主义的进路,至少应当强调三点:其一,自我建构。行政自制存在于行政系统内部,通过各种内设的机制来完成,而无论行政系统整体还是各种内设机制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按照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必须充分发挥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调节功能并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到达最佳的建构。行政自制就应当成为这样一个通过自我建构、自我调节而到达自我控制的体系。其二,原则之治。功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则之治”。行政自制并非不受“法的约束”,只不过这种“法的约束”主要来自法律原则,因此行政自制应当是以法律原则为取向的自我控制。其三,融合“他制”。行政自制并不是“自我封闭”,强调自制并不能排斥“他制”。按照功能主义,这种行政自制既应当被置于“框架性立法”之下,也要接受变化了的司法审查,即作为“过程控制”而非单纯“法律控制”的司法审查。同时,功能主义既要求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也要相互制约,所谓“独木难支”,只有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才能形成有机整体。因此,行政自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并获得正当化的源泉,不仅要以立法功能为前提并以司法功能做保障,而且其内在的制度设计不能完全排除“他制”要素的嵌入;不仅各种内设机制之间应当相互联动、协调一致,也应当适当注入民主的公开与参与,成为一种开放对话的建构过程。
可见,“功能主义”可以也应当成为行政自制这样一种新型控权理论的根基或最基本的理论支撑。迈向一种功能主义的行政自制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的行政自制,作为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新路径,必将更加大有作为。
-->| 【2004新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 【118图库免费资料图】 |
| 【2024年新澳门天天开彩免费资料】 【7777788888精准新传】 |
| 【2024年正版免费天天开彩】 【黑龙江一客车发生单方事故】 |
| 【2024新澳今晚资料】 【2O24年澳门正版免费大全】 |
| 【2024新澳免费资料三头67期】 【2024澳门天天彩期期精准】 |
| 【2024新澳正版免费资料大全】 【2024澳门今日】 【2024新澳门天天六开好彩大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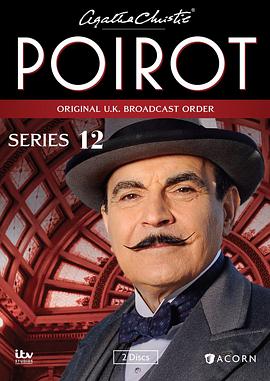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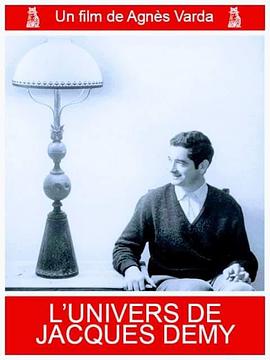







发表评论
Mihika
9秒前:(注: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第76页。
IP:82.18.6.*
亚历山德拉·希普
9秒前:2.
IP:89.33.6.*
Salmaan
1秒前:实际上该认识只是看到了裁量基准的形式特征,而没有注意到其实质的控权逻辑,其在属性定位上存有片面性。
IP:91.46.4.*